與《紅樓夢》思想深刻密切聯系的,其作品蘊涵着極為飽滿的情感因子,這也是作品明确提出的“大旨談情”。對于這種“談情”,有人從《紅樓夢》的抒情傳統角度(如周汝昌),有人從《紅樓夢》的色、情、空辯證關系及文化精神角度(如孫遜),有人從“有情之天下”(葉朗)角度加以了總結。但是,從所謂的“禮出大家”角度,從中國傳統的禮儀文化與“情”的相生相克而顯示的整體性意義,并沒有得到充分揭示。
“大旨談情”給小說帶來的總體上的情感飽滿,其所謂的“情天情海”,有其更大背景上的文化意義。簡單地說,明清之際,當沿襲甚久的儒家禮儀文化漸趨沒落時,當維系人與人關系的禮儀變得日益脆弱或者虛僞時,當以理釋禮的理學家的努力并不能得到更多人信服時,提出“大旨談情”的問題,就成為作者對維系人的良好關系可能性的重新思考,也是對人的情感狀态的各種可能性的重新構想,對人的心靈世界的深入開掘。這樣,小說呈現的人物的多樣、情節特殊化以蘊含的思想深刻等方面,都在情的滲透中,得到了重新建構和理解。而情感的飽滿,又是以其豐富性、語境性和變通性來獲得充分體現的。
(1)情感的豐富性
據脂批透露的信息,曹雪芹原打算在小說結尾,以一張“情榜”給出的情感方面的評語來對各類女性人物加以分類概括的。這樣,人物的多樣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對人的情感類型的細細劃分,體現出作者對人的心靈世界有關情感問題的豐富認識。盡管我們并不知曉“情榜”中的所有人物評語,但即以脂批透露的賈寶玉和林黛玉評語來看,寶玉是“情不情”,黛玉是“情情”,前者指對不情之物,也傾注情感,後者則以情感來對待有情之物,這樣,前者側重于情感的廣度,後者主要體現情感的深度。這種區别,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傳統社會的男女不同的情感特質,予以了提示。我們還可以借助“金陵十二钗”冊子的序列,來發現賈寶玉與周邊女性交往的情感差異體現的豐富性。如前所說,“金陵十二钗”正冊的前後序列是依據與賈寶玉的親疏關系而展開的。有學者也曾經以親情、愛情和友情等類别來加以歸納的,這當然也是一種思路。但如果進一步細分,把不同女子依托的文化修養及其言行舉止來重新思考,那麼,除開同胞姐妹外,就以賈寶玉身邊最親近的四位女子論,黛玉的熱烈、寶钗的含蓄、湘雲的自然、妙玉的做作,諸如此類,可以讓我們驚訝發現,男女之間的情感交流,在《紅樓夢》展開了如此多姿多彩的風貌。
同樣,當飽滿的情感充溢于情節時,傳統小說側重于故事、傳奇的動作性沖突悄悄退後了,帶來心靈震蕩的情感之流裹挾着瑣碎的細節,成為與故事性的情節并立的另類叙事。于是,在這樣的意義中,看似平淡無奇、毫無沖突可言的黛玉葬花舉動,比如第二十七回的“飛燕泣殘紅”,因為情感的宣洩形成了高潮,于是就成了幾乎可以與“寶玉挨打”這一相當重要的情節高潮分庭抗禮的又一個高潮。也因為這個原因,後來越劇改編的《紅樓夢》,把黛玉葬花内容移到寶玉挨打之後,讓它成為人物命運發生逆轉前的一個高潮。而在思想深刻方面,作者在直面家族衰敗的真相、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不幸的命運方面,也因情感的真誠和飽滿獲得了巨大的内驅力。關于《紅樓夢》描寫人物情感的豐富性,這裡隻想舉一點來說明,《紅樓夢》在表現女性的醋意或者說妒忌之情時,同樣體現出作者獨到的思考和有關人物情感的豐富想象。

林黛玉,選自《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多愁多病身”出自《西廂記》,形容張生體弱,與指崔莺莺的“傾國傾城貌”對仗,這裡借指黛玉體弱敏感
傳統的男子中心主義、不合理的妻妾制度以及出于家庭内部穩定的需要,嫉妒的女性成了曆代被嘲笑的對象,不但有《妒記》一類的筆記小說,還有如《醒世姻緣傳》那樣把妒婦塑造成惡魔般的可怕形象。但像俞正燮《癸巳類稿》中提出的“妒非女人惡德論”那樣的話題,還是比較少見的。而《紅樓夢》在對女性的嫉妒表現,給出了不少具體描寫。雖然作者也描寫了妒忌的男性如賈環等,但遠不及描寫的妒忌女性那樣生動而多樣,其蘊含的獨特價值判斷,也足以令人深思。
清代的蔡家琬(别号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随筆中,曾把大觀園視為是一個醋海。他寫道:
大觀園,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渾含者,寶钗也。醋中之活潑者,湘雲也。醋中爽利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覺者,襲人也。迎春、探春、惜春者,醋中之隐逸者也。至于王熙鳳,詭谲以行其毒計,醋化鸩湯矣。曾幾何時,死者長眠,生者适成短夢,亦徒播其酸風耳。噫!
其對各人的概括是否正确暫且不說,但其分出的不同類别,可以提醒我們,小說在多樣化刻畫女性人物情感時,妒忌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子。作者的獨特性在于,小說一方面沿襲了傳統習慣,塑造了奇妒女子夏金桂,表現出對此類女子的厭惡。但與此相對照,小說還塑造了似乎大度無私、一心為丈夫張羅小妾的賈赦之妻邢夫人,同樣令人反感。這樣,究竟如何判斷女性的妒忌或者大度,就不再像傳統那樣,出于男子中心主義的價值觀,能夠給出一個絕對的判斷。因為,在曹雪芹筆下,女性的妒忌問題,既跟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相關,也跟不合理的奴婢等級制度有關,當然,還跟男性自身用情不專一甚至淫欲無度有關。這樣,嫉妒,往往成了女性鞏固自己地位的武器。如鳳姐,既有對鮑二媳婦的大打出手,也有針對尤二姐的設計毒害;而夏金桂對于先她而在的香菱,不但在肉體上予以打擊,也對其詩意生活的向往竭盡嘲弄之能事;或者如襲人,對寶玉把海棠花比作晴雯也堅決予以否認。但有時候,嫉妒也可以對男子用情不專一加以情感校正,比如黛玉不時流露的醋意,就提純了賈寶玉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讓“見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寶玉變得用情專一起來。就這樣,小說在充分展示這種複雜性時,使得僅僅是表現人物妒忌這一類情感時,也顯得相當豐富和辯證。
有學者認為,邢夫人貌似寬容大度不同于鳳姐的妒忌強悍,是因為邢夫人娘家已經敗落,無法跟當時仍然顯赫的王家相比。這種力圖揭示人情背後的權勢因素,也是在努力理解小說展示情感的一種依附性,這正是情感書寫折射出的社會性一面,值得我們進一步讨論。

王熙鳳,選自《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榮府掌權者,“酸醋當歸浸”,言其醋意大
(2)情感的語境性
《紅樓夢》雖然“大旨談情”,但這種情感又不是在真空中進入人物内心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習俗、禮儀制度等作為維系人們日常行為的基礎和規範依然存在,于是情感的抒發和交流,就常常是在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制約中相生相克,一旦呈現到衆人面前,就折射出社會風貌的深廣度,體現出它所依存的語境性。盡管以往的才子佳人小說涉及人物情感時,也都是在語境中産生的,但其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叙事模式,在語境的呈現方面基本是把特定社會風貌抽離出去的,如果說這也是一種語境的話,那麼這樣的語境是抽象的,是較少能夠反映特定社會環境和人物複雜關系的,而《紅樓夢》則不然。下面舉例來分析。
第五十四回寫賈府過元宵,寶玉要來一壺熱酒,給老祖宗等衆長輩敬酒,老祖宗帶頭先幹了,再讓寶玉也給衆姐妹斟酒,讓大家一起幹。想不到黛玉偏不,還把酒杯放到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幹,黛玉笑說:“多謝”。接下來寫鳳姐也笑說:“寶玉,别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拉不得弓。”寶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
對此,有學者在點評中比較了黛玉和鳳姐的笑,認為“黛玉對寶玉的‘笑’是知心,一個動作,對方就心知肚明。王熙鳳對寶玉的‘ 笑’是關愛,姐弟深情”。也有紅學家認為“寶玉已知其體質不宜酒,故代飲。兩心默契,寫來出色”,前一點評認為是體現鳳姐對寶玉的姐弟情,後一說法,強調了寶黛間已成默契的情感。細細推敲,似乎都不夠精準和全面,因為都忽視了人物依托具體語境顯示的特殊意義。
不可忘記的是,前文已經交代,寶玉是拿熱酒敬大家,他代黛玉喝下的,正是同一壺中的酒。鳳姐居然叮囑他别喝冷酒,還把喝冷酒的後果帶着誇張的口吻說出來。更離奇的在于,當賈寶玉聲明自己并沒喝冷酒時,鳳姐又馬上說她也知道,不過是想囑咐他一下,這裡,白囑咐的“白”,有着“隻、隻是”的意思,就像第三十四回寫的:王夫人道:“也沒甚麼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那麼,在這樣的語境中,鳳姐說了一句無的放矢的廢話,似乎與她為人的一貫聰明并不協調,這是為什麼?無論說是體現“姐弟情深”,還是寶黛間的默契,都沒有把語境的完整意義概括出來。
如果換一種角度看,當大家都在順着老祖宗的要求喝完寶玉斟上的酒時,隻有黛玉例外,反要寶玉替自己喝,雖然就寶黛他們兩人自身言,當然可理解為是關系融洽,但對于在場的衆人,未必會認同這一幕,更何況這是在跟老祖宗唱反調。所以,清代評點家姚夑認為,“當大庭廣衆之間偏作此形景,其賣弄自己耶?抑示傲他人耶?”對黛玉此舉頗有微詞,而洪秋藩則将黛玉與寶钗比,認為黛玉“大庭廣衆之中,獨抗賈母之命,且舉杯送放寶玉唇邊,如此脫略,寶钗決不肯為”。所以,王希廉認為“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姚夑說“鳳姐冷眼,遂有冷言,故曰别吃冷酒”,諸如此類的判斷,都是較為精當的。這樣,讓寶玉别吃冷酒,指向的并不是酒,因為酒确實不冷。倒是容易讓人産生一種聯想,就是黛玉與寶玉間看似情深的親熱行為,不但有抗命賈母的嫌疑(盡管寶玉和黛玉都是賈母的心頭肉,她似乎不便也不願意當衆指責他們),而且如此大庭廣衆下“秀恩愛”,在傳統社會也涉嫌非禮。于是,鳳姐的言說恰是在針對寶玉的表面熱切關心的無意義,似乎說了也白說,才顯示了轉向黛玉的冷嘲意義。
把王熙鳳此處的冷嘲,與第二十五回一段描寫王熙鳳直接打趣黛玉對照起來看,就更清楚了。那段打趣,是因為黛玉吃了王熙鳳送來的茶所引發:
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們家一點子茶葉,便來使喚了。”鳳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說這些閑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 ,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來。林黛玉紅了臉,一聲兒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
這裡,王熙鳳拿黛玉的婚姻大事打趣,也許并不合适,但因為是泛泛之語,而且這種打趣,多少揣摩了賈母喜愛黛玉的心思,所以也不算太失禮,甚至這種打趣,還有示好的意味。隻是如果寶玉和黛玉要把這種泛指落實為具體的“秀恩愛”行動,甚至違背了賈母讓大家都自己喝光酒的要求時,這才引發了鳳姐的冷嘲,以收敲打黛玉的效果。這樣,作者寫人物的情感表達和交流,跟他們是否合乎禮儀的規範以及能否體貼長輩的孝心結合在一起了。如果剝離開這種語境,認為僅僅是體現鳳姐對寶玉的關愛,或者寶玉和黛玉的默契,隻盯住情感來讨論問題,都是流于表面了。

黛玉焚稿斷癡情,選自清《紅樓夢賦圖冊》
(3)情感的變通性
提出情感的變通問題,可能會讓人驚訝。情感難道不是不變才有價值和意義嗎?文學作品不是一直在讴歌這種“江流石不轉”的情感的永恒性嗎?但如果我們進入《紅樓夢》具體人物關系時,發現作者恰恰對這種變通有自己獨到的理解和描寫。這種理解和描寫,主要體現為對承載着人際情感的“一”與“多”的現實關系中。
賈寶玉剛上場,其所具的“好色”“怡紅”特征,表現在喜歡林黛玉的同時,也對許多年輕女子魂牽夢繞,黛玉所謂“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雖是一句吃醋的話,但也不能說是空穴來風,一點沒道路。事實上,第十九回,寶玉希望襲人的表妹也到他身邊來,第三十六回,當寶玉向襲人講自己的人生追求,是要一群姑娘的眼淚來埋葬他時,其内心深處,還是有那種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男子中心主義在盤旋,對女子還是有一種普遍占有欲的情結在作怪。不過,賈寶玉并沒有止步于此。他是在跟演戲的齡官交往碰壁中,在看到齡官與賈薔癡情交流的一幕後,反思了自己的情感定位,從而讓他從男子中心主義的幻覺中走了出來,于是就有了這樣一段對賈寶玉情感調整來說極為重要的描寫:
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歎,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隻是各人各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隻是每每暗傷,不知将來葬我灑淚者為誰。

賈寶玉,選自《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紅樓夢》核心人物,怡紅公子。“俏東君與莺花作主”,言其最愛惜女兒
對于寶玉這樣的情感覺悟,又不能簡單理解為他認同了從一而終。盡管他是情種,但對情人間的關系相處,又持有較為通達的看法。第五十八回,寫十二戲官中演小生的藕官和扮演旦角的菂官假戲真做,旦角去世後,哭得死去活來,不忘祭奠,但是對于後來頂替的蕊官又是一往情深,引得周邊同伴嘲笑她喜新厭舊。她回答是:
“有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續弦為是;但隻是不把死的丢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雖然這番議論被作者稱為是“呆話”,但又說恰恰是合了寶玉的“呆性”,讓其又喜歡,又感歎。在這裡,我們固然可以認為作者并不認同“從一而終”的情感關系,但畢竟,藕官是以男子身份來談續弦問題的,而“從一而終”又常常是對女子的要求,那麼,這樣的變通要求,是否也隻是一種男子普遍占有欲下的變通處理呢?也許不一定是。可以舉兩個正好相反的實例來說明。
第一,小說似乎對寶玉大嫂李纨青年守寡的生活方式,未必一定認同。雖然我們找不到直接的依據,但賈寶玉在大觀園落成題匾額時,對後來是李纨的住所稻香村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這處所的整個設計違背了自然的原則,考慮到大觀園中各處院落,與居住的主人趣味品格等有一定關聯性,那麼,稻香村的反自然,是不是跟李纨違背自然人性的守寡,有一定的契合度呢?作者是想這麼來暗示讀者嗎?
第二,小說中後來寫到的尤三姐是以一個淫奔女的惡名立志改過自新,與柳湘蓮厮守一生的。但柳湘蓮基于男人的自私和虛榮,以不做“剩王八”的所謂尊嚴,徹底拒絕了尤三姐自新的機會,導緻尤三姐絕望自殺,柳湘蓮醒悟過來後出家了事。在這件事中,作者站在所謂“不幹淨”的尤三姐的立場上是明确的,不含糊的。這樣的一種情感變通立場,不是以教條式的貞潔來要求一個弱女子的思想,出現在《紅樓夢》中,是難能可貴的。
本文節選自“中華經典通識”系列之《<紅樓夢>通識》,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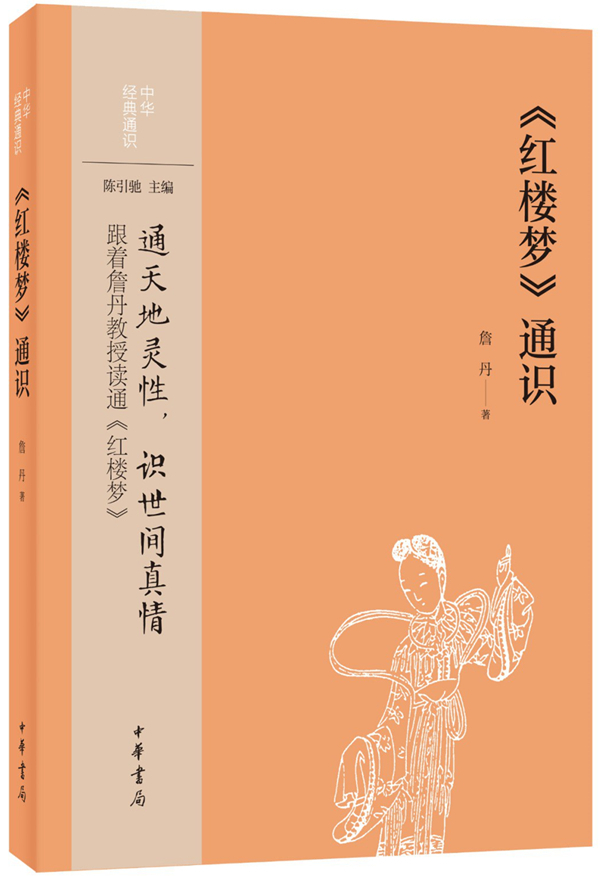
《<紅樓夢>通識》,詹丹/著,中華書局,2022年7月版
鍊接地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955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