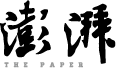
張劍光:唐五代江南史研究的若幹問題
張劍光
2019-05-04 16:47
緣起:本文是接受一個報社記者的通信采訪,他為我列了近十個題目,而我挑選了其中四個作答。由于我沒搞清記者的真實編輯用意,寫了好幾頁發過去,沒曾想記者是一組采訪合在一起,隻從我的稿子裡面挑了幾段話。由于不想浪費自己的成果,所以幹脆對文章重新進行思考,增加了資料和出處,對有些段落進行的改寫。
盡管唐五代江南史一些基礎問題的探索取得不少成果,但學術界對江南曆史的思考仍在繼續,并不斷推進。前不久,一位先生向我提出了若幹研究中他在思索的論題,希望我也能作些回應。這些内容,的确是以前我在研究中沒有進行太多的思考,或者是研究中涉及到了,但沒有系統地作為專題提出來,因而在考慮中顯得比較薄弱。今天把這幾點思考寫成文字進行回答,力圖想解決這幾個江南史研究中的問題。當然,我的思考肯定還有不夠成熟的地方,隻是想提出來供大家一起讨論。
一、唐代的江南有多大
安史之亂後,詩人杜甫在他鄉重逢舊友李龜年,寫下了《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李龜年是開元年間宮裡的著名樂工,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特承顧遇”,安史亂後流落湘潭。研究杜甫詩的學者認為杜甫此詩寫于天寶之後,作于潭州。如此看來,杜甫說的的江南是指唐代中期今湖南一帶。
稍後一點,詩人白居易有《憶江南詞三首》,其中第二首說:“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第三首說:“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杯春竹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複相逢!”前者指杭州,後者指蘇州,白居易的江南顯然是指長江下遊地區。
其實唐代詩人以“江南”為題的詩歌還有很多,比如李群玉、羅隐有《江南》,于鹄、李益、儲光羲有《江南曲》,張籍、杜牧有《江南春》,仔細地看一下他們的詩,發現詩人筆下的江南并不是完全一緻的。當然詩人所指也有共同的地方,即談論的地域都是在長江以南。實際上,就唐代而言,“江南”是一個特殊的概念,并不是固定不變的,這個概念在不斷變化,因而人們的所指并不完全一樣,範圍有大有小。
秦漢以後,一般“江南”指今長江中遊以南的地區,主要指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而長江下遊的今皖南、蘇南一帶,因為長江大體是呈南北走向,常以“江東”著稱。如周振鶴認為這一時期“江南的概念大于江東”、“江南其實還有江漢以南、江淮以南的含義”。李伯重的觀點稍有不同,他認為江南是個地理方位,“并非有明确範圍的地域區劃”,長江以南都是江南。在開皇八年诏書中,隋文帝談到:“巴峽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為鬼為蜮。”這裡的“江南”應該是指長江中下遊廣大的長江以南地區。六朝定都建康,北方人稱南方政權為江南,長江下遊自然是被作為江南的一部分。如卷四八《楊素傳》談到“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為亂”,而作亂的江南人大多在京口、晉陵、蘇州一帶。長江下遊的長江以南部分除稱為江南外,也稱為江東、江左、江表。如《隋書》卷二《高祖紀下》隋炀帝開皇八年,文帝的诏書談到“有陳竊據江表”,卷四八《楊素傳》談到“上方圖江表”。
“江南”這個地理方位概念,到唐代成為一個具體的地區概念,被指稱為固定的地域。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将天下分為十道,長江以南嶺南以北的廣大地區為江南道。周振鶴認為這時的“江南”應該是最名符其實,長江以南地區全部稱為江南,包括原先所稱的江東地區。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為十五道,江南道分成江南東道和江南西道、黔中道。江南東道治所在蘇州,時人将其簡稱為江東,江南西道治所在洪州,時人将其簡稱為江西。中唐以後,江南西道一分為三,自西至東依為湖南道、江南西道、宣州道。宣州道相當于今皖南地區,後改稱宣歙道。江南東道也屢有分合,最後一分為三,分為浙江西道、浙江東道和福建道。杜甫詩歌所指的時期,就是唐代從盛轉衰的天寶之後,因而他所用的概念,實際上是唐代前期的,江南當然是包括湖南地區。即使是開元後期江南道一分為二,湖南道仍然是在江南西道中,因而稱其為江南是合乎當時的實際情況。

然而,正是在唐代中後期,“江南”這個地理方位概念與行政區劃的漸漸結合,“江南”概念的内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人們所指的江南常有寬狹多種稱法。寬者,沿用傳統稱法,如杜甫一樣,用唐前期的江南道概念,即使在政府的一些文書中稱江南,仍然包括今江西、湖南地區。唐文宗(827-840)在《令禦史巡定諸道米價敕》中談到派禦史“于江南道巡察”,但這個江南道卻是包括了“江西、湖南、荊襄”。即使到了五代後期,在金陵建立的南唐,常被北方的國家稱為“江南”,而南唐實際控制的地盤主要是今江西、皖南和江蘇淮河以南地區。唐代末年,莊布訪皮日休,因故沒有見到,遂“以書疏其短失”,結果大家都想争着看這篇罵人的文章。皮日休的兒子皮光邺,“嘗為吳越王使江南,辄問:‘江表何人近文最高?’”沒想到有人說最流行的是莊布贈皮日休的一篇文章,“光邺大慚”。南唐被稱為江南、江表,實際上沒有使用嚴格意義上的行政區劃概念,而是沿用了傳統,長江以南皆稱為江南。
也有人将“江南”專指江南西道。如天寶五年,唐玄宗在一個敕文中談到,韋見素“巡山南東、江南、黔中、嶺南等道”,而另一位官員“巡淮南及江南東道”,将江南和江南東道對應,顯然江南是專指江南西道。陸羽《茶經》卷下《八之出》中并列談到浙西、浙東、江南三個概念。其時宣歙劃進了浙西,因而他的江南是指今江西及以西地區,内中包括了鄂州、袁州、吉州等,江南實際上指的是江南西道,而江南東道在中唐人的眼裡是兩浙。一些帝王的诏書中将江南和浙西、浙東、宣歙并列。如大曆元年常衮為代宗寫的《命諸道平籴敕》談到各道要設多少防秋兵,“其嶺南、江南、浙西、浙東等,亦合準例”,江南就是單指江南西道。唐穆宗長慶二年派盧貞“往浙東、浙西道”,李行修“往江南、宣歙等道安撫”,這裡的江南與代宗敕文中所指範圍完全一樣。當然,人們更會将江南西道簡稱為江西。如懿宗鹹通三年的《嶺南用兵德音》中,談到“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簡”,應該是當時最常見的用法。
不過中唐以後,一個重要的變化是,有很多人稱的“江南”專指浙東、西和宣歙三道。如《舊唐書》卷一四《憲宗紀上》曾談到唐憲宗元和三年“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江南和江西并列,就隻能是指江南東道地區。皇甫湜談到顧況“從韓晉公于江南為判官”,“入佐著作”,“為江南郡丞”。韓滉于建中二年五月任鎮海軍節度使、浙江東西道觀察等使,直至貞元三年二月卒于任上。據《新唐書•方鎮表五》,建中二年時,“合浙江東西二道觀察置節度使,治潤州,尋賜号鎮海軍使”,因此皇甫湜談到的“江南”實際上是指浙東、浙西地區。宰相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為亡妓謝秋娘作曲,本名《謝秋娘》,後改名為《望江南》,亦稱為《夢江南》,宋人指出:“蓋德裕所謂江南多指京口”,“大率唐人多以潤州為江南”。這兒的江南就是指兩浙地區。
唐代後期,江南的概念實際上并沒有固定下來,有大小之分,按目前史書中的記載,既有用傳統的說法,又有指江南西道,但更有指稱浙東、西和宣歙三道。其中指浙東、西和宣歙為江南的雖是後起,卻漸漸被人們接受,而且使用上越來越多。北宋至道三年(997)全國被分為十五路,唐代的浙東、浙西劃分為兩浙路,宣歙道及唐代江南西道地區劃分為江南路。江南路分為東路和西路,江南東路指江甯府、宣州、歙州、江州、池州、饒州、信州、太平州等地,簡稱為江東路,而江南西路大體與今江西相當,簡稱為江西路。兩浙路的地域是指今鎮江以東的蘇南地區,加上浙江全境。由于行政區劃的變化,宋代人的“江南”概念仍然不定,有時稱江南路,有時稱兩浙路,而一些人幹脆直接稱為“江浙”。當然,更多宋代人所指的“江南”,漸漸移向兩浙,兩浙路成為江南的核心區域。
總體看,“江南”這一概念所指地區有越來越小的趨勢,但唐末五代至宋初,還沒有完全固定下來。不過将江南指向兩浙地區,已為更多的人所認同和接受。
二、江南社會風氣是怎樣轉變的
江南地區自古以來社會風俗是以勇猛善戰而著名的。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中談到吳地人“皆好鬥,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此後人們一直認為“吳阻長江,舊俗輕悍”,“吳人輕銳,難安易動”,江南人“好劍客”,“好劍輕死”。南宋範成大編《吳郡志》時,發現了這個問題,說:“華誼論雲:‘吳有發劍之節,趙有挾色之客。’《郡國志》雲:‘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鬥将戰士。’按諸說吳俗,蓋古如此。”不過這種局面到唐代的史書裡發生了轉變,談到江南人是“俗好儒術,罕尚武藝”,“人尚文”,“吳人多儒學”,說明從唐代以後,江南地區的社會風氣有着根本性的轉變。
這種轉變到底是什麼原因?我認為應該和北方士人的遷入和江南學校教學的興起有關。此外與宗教化民成俗的功能也有一定聯系。
西晉以後,為躲避戰亂,北方的衣冠大族紛紛南渡,将北方文化的精華和傳統帶到南方,江南是南遷北方人較為集中的地區之一,而且他們往往又是政權的把住者,因而在他們的影響下,江南的社會風氣大有改觀,風俗澄清,“道教隆洽”。如東晉餘杭縣令範甯“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己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那些在政治和經濟上有較高地位的士人自然想讓自己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江南學校制度的建立就有了社會條件。士大夫階層以崇尚禮儀相标榜,他們使社會走向“慕文儒,勤農務”的良好風氣。當然,要使社會面貌改變畢竟不是一朝一夕的,六朝時期的教育制度并不夠完善,教育對社會風氣的改變隻是初步的。唐人說:“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裡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郁也久矣乎。”
唐代,北方衣冠大量來到江南,對南方的社會禮儀規範有重要影響。如蘇州是北人南遷的重要聚集地,史雲:“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笃厚。”就連唐末溫州也有很多衣冠居住:“隋唐闡海隅之化,而江浙盡為衣冠。”南唐時,都城金陵士大夫更為集中。宋人雲:“江南當五代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于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南遷士族對社會風尚的形成作用十分明顯。

唐代,江南各州縣都建立起學校制度,盡管州縣學的規模一般,政府并沒有更多發展學校的具體措施,但教育事業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在學校教育制度、學校教育管理以及教育理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創新意識,這些畢竟對社會風氣的變化産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蘇州州學,李栖筠為浙西都團練觀察使時,“又增學廬”,擴大規模,并延聘名師執教,河南的褚沖和吳何員等大儒從北方前來任教,将不同的學術觀點帶到學校,使學術争鳴和探讨有了條件。蘇州州學按規定隻能有學生60人左右,結果“遠迩趨慕”,學生有數百人,是中央政府規定人數的幾倍。之前,李栖筠在常州就有大辦教育的舉措。代宗永泰年間他任常州刺史,在夫子廟西“大起學校”,估計也是擴大校舍,增招學生,因而我們看到唐代中期的常州是“文治煟如也”。再如唐代昆山縣學經縣令王綱重建後,人們紛紛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學校學習,而且還“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不接受學校教育就會被人瞧不起。
此外,民間私學發展較快,既有士大夫家裡的家庭教學,又有個人私相傳授的私學,同時在一些鄉村地區有一定規模的鄉學。這樣的重視教育,到北宋更進一步,“時州将邑長,人人以教育為己職”,《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認為“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如歐陽修在《丁君墓表》中說:“慶曆中,诏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丁寶臣“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于鄉裡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大量興辦學校,使得江南人才輩出,文化素質提高,江南辦學傳統至宋代可以說完全建立。
重視教學的風氣形成,直接導緻文人士子文化素養較高,讀書人在隋唐開始的科舉考試中不斷取得成功,如蘇州、常州等地區,中進士和明經的人數特别多。蘇州唐代進士及第有50多人,單狀元就有7位,常州的進士、明經也有數十人。顧宏義據《文獻通考》卷三二《選舉考五》等材料統計出北宋時期,平江府出狀元1人,常州府2人,湖州府1人,南宋時平江府出狀元3人,常州府1人,共計8人。在全國共118位狀元中,吳地占了6.8%左右。教育的成功,促進了民衆的文化水準普遍提高,更多的人參加科舉考試,并進入官僚隊伍。重文重教育的風氣,徹底改變江南的社會風氣,到了北宋以後,江南士人幾乎是人人崇尚教育,從而造成人才輩出。完備的教育體系,有效地發揮了學校教育在教化育民、化民成俗方面的政治功能,同時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官吏,有效地解決了讀書人的出路問題。毫無疑問,學校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江南社會尚文風氣形成的重要因素。
江南地區自南朝以來養成了喜淫祠、好佛道的風氣,宗教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對民衆文化意識的變化産生重要影響。到了唐代,江南民衆更是利用神靈消災怯病、賜福避禍,他們希望神靈提供一個風調雨順的生活和生産環境,來保證他們生産豐收、生意興隆。蘇州東阊門之西有泰伯廟,“每春秋節,市肆皆率其黨,合牢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彩輿、女子以獻之,非其月也無虛日”。這種神靈信仰,一方面是民衆文化意識的一種傳承,百姓為了追求精神上的寄托,向往美好生活,對衆神敬仰發自内心,另一方面,衆神信仰有着濃厚的現實意義,很多供奉的神靈都是以前的一些官員,他們在任期内政績顯著,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因此後人就紀念他們。佛教的教化功能南朝至唐代表現十分突出,江南百姓向往佛國樂土,如佛教中的淨土宗在唐宋之際漸漸把發展重心移向江南。杜牧談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宋人談到佛教流入東南,“梁武帝事佛,吳中名山勝景,多立精舍。因于陳隋,浸盛于唐”。佛教提倡的很多教義,滿足了普通老百姓對人生的追求和向往,對江南的民風民俗的改變有着一定的作用。可知,唐五代時期,宗教對民衆文化意識的形成和變化産生了重要影響,江南民衆常常會以自己特有的态度以及與此相适應的方式來創造各種神靈,賦予它們不同的神性,來護佑自己的生活。這種特有的宗教氣息,對各種信仰的依戀,必然會影響整個社會的風氣。
江南百姓重教育、廣信仰的特點,決定了他們好文輕武的性格特征其本形成,從而造成很多人做事講究條理,遵守種種官私法規條例,安分守己,外表敦厚,内在堅強,向往美好生活,堅信通過自己的勤勞能獲得幸福生活,很少想用暴力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當安史之亂發生後,浙西地區出現了一些外來兵變形成的騷亂,而内部的民變很少,因為缺乏社會基礎,江南的文化傳統往往決定了人們不願反叛政府,隻願靠自己的努力來創造美好生活。
不過,在江南唐宋以後形成的重文重教風俗的同時,還有一種重商崇奢風氣也在漸漸出現。唐代以後,江南地區城市商業經濟繁榮,城市服務性行業蓬勃興起,城市商業對周圍的輻射力增強,城市内出現了特殊消費階層。城市内聚集了很多士大夫、文人、富豪和官員,他們在城市中過起奢侈的生活。大城市中消費階層的龐大,必然對城市經濟有所要求,對社會風氣産生較大影響。呂溫曾雲:“天寶季年,羯胡内侵,翰苑詞人,播遷江浔,金陵、會稽文士成林,嗤衒争馳,聲美共尋,損益褒貶,一言千金。”應該說,這是對江南出現城市消費階層的準确描述。江南社會相對安定,經濟繁榮,為富豪文人的醉生夢死提供了優越的外部條件,因此“江外優佚,暇日多飲博”,飲酒作樂、遊玩山水。如杭州是文人士子遊玩的一個好去處,杭州刺史李播曾說:“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即使到五代時期,廣陵王父子周圍仍有一大批文人在蘇州玩樂飲酒。宋淩萬頃《淳祐玉峰志》卷下雲:“洛陽衣冠所聚,故多名園;夜市菱藕、春船绮羅,則足以見吳中遊适之盛。”随着大批北方人的到來,他們将自己的愛好帶到了江南,江南城内興起了建築園林的高潮。
江南地區的農業,也是商業化意識濃重。水稻等糧食作物大面積種植,培育出了許多優質品種,有的純粹是為了商品生産而種植;江南糧食販運至全國各地,不但遠距離的糧食販運貿易相當興盛,而且在江南本地市場的銷售亦十分繁盛,一些地區的糧食缺口往往是靠市場來補充。江南種植了大量的經濟作物,呈現出了規模化的特征。随着江南人口的不斷增多,各級市場的擴容,對農副産品的需求量增大。農業生産商品化的趨勢和農産品商品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是農業生産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對江南社會起着重大的影響,促進了江南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地方市場的勃興,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市場的廣泛出現是一個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标明了江南商品經濟達到了一定的水準。集市是農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城鄉市場聯系日益加強、各地區之間商品流通趨于活躍的産物。農村集市的大量湧現是江南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晶,它設置在縣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區和交通便利處。這種自發産生的集市一般稱為草市,也稱野市、小市、村市、橋市等。還有一些在特殊商品出産地附近出現的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如魚市、桔市、茶市等。我們發現,唐代江南有明确名稱的草市約20多個,主要分布在潤州、常州、蘇州、湖州、杭州、越州,基本上集中在江南北部,是江南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農村市場的廣泛出現,對唐代江南農村社會帶來了較大的影響,使大量的農民自覺或不自覺地進入商品生産領域,卷入到商品生産之中。受市場商品的需求影響,為追求利潤,一些農民改變了農作物的種植結構,改變了農作物的品種。一些農民直接面對市場,他們按市場的要求來調整生産計劃和品種結構,以實現農産品的商品化,獲得更多淨收益。至兩宋時期,農村市鎮大量出現,而且不少市鎮帶有區域色彩,商品都是江南特有的紡織品和魚鹽,使農村地區商業全面繁榮。
從曆史的傳承看,自唐至宋元明,社會重文、重商的風氣其實是一脈相承的,這種風氣總體上并沒有中斷,而是一個逐漸的累積過程。唐代的重文風氣改變了兩漢前的重武風尚,而宋代的重文風氣随着科舉名額的擴大和學校大量的建立,其影響更為深刻和廣泛。重商重奢的源頭,應該是在唐代,但宋明時期随着城市和農村商業的發展,這一特點顯得更為明顯。這樣的社會風氣,在江南并沒有中斷,相反随着唐末宋代北方士大夫的不斷南下,商品消費的擴大,重文和重商的風氣更為加強和流行。

三、唐前期江南的經濟水平有多高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戶口大量增加,經濟發展快速,社會财富大量積聚,富裕程度提高,再加上社會秩序平穩,唐朝處于發展的頂峰,人稱“開天盛世”。杜甫《憶昔》對這種富足有詳細的描繪,雲:“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廪俱豐實。”這樣的一種社會殷實富足,并不是詩人的故意誇張,而是真實的社會狀況。不過,我們要問的是,同時期的江南也是這樣的富足?抑或是另一種狀況?以往,我們一直認為江南的開發是安史之亂以後的事情,開天盛世主體是指北方經濟的發展和繁榮,那麼,江南的情況如何呢?
唐初,經過了動亂之後的江南地區人口比較稀少。我們根據《舊唐書》卷四○《地理志》、《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的記載,可以看到江南道各州每平方公裡人口密度,依次為杭州(18.97)、潤州(16.05)、常州(13.17)、湖州(11.86)、婺州(10.81),越州、睦州、蘇州、括州、台州都不到10人,最低的台州隻有2.92人。
當北方出現開天盛世時,北方的戶口數達到了唐朝曆史上的頂峰時期,而江南各州的戶口數,我們發現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幅度甚至超過北方。和貞觀十三年相比較,至天寶元年,江南地區戶增長率為381.2% ,口增長率為538.3%。同期全國戶增長率為195%,口增長率為312.7%。如果按人口密度來看,江南一些地區的變化更是驚人。如常州每平方公裡人口增長了68.3人,潤州增長了67.7人,婺州增長了56.6人,杭州增長了53.3人。每平方公裡的人口達50人以上,農業基本發展需要的人口數實際上已經足夠。如果超過或接近100人,大體已經達到農業精耕細作的需要。實際上江南地區在開元天寶年間,不少地區的農業生産已經告别粗犷型的發展,開始向精耕細作的方式轉變。江南地區人口的增加遠遠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說明江南地區的農業必然是進入了一個快速的發展時期。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認為天寶年間江南人口的猛增,“應是農田水利工程建設、育種史上的技術革命以及交通的發達”等原因導緻的。反之,人口的快速增加,必然會導緻經濟的向前發展。
一般認為,唐代前期的水利建設主要集中在北方,但中唐以後南方不少地區出現水利建設的高潮,水利建設的重心移到了南方。如果說這是整個唐代的大緻情況,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具體到每個階段,水利建設的局面卻是各具特點。
浙西和浙東在唐代共有96項水利建設工程,其中唐前期有21項。唐前期有1項時間不詳,其他的20項中,主要集中在高宗武則天時期7項,玄宗時期9項。如果我們與同時期北方主要農業地區進行對比,還是可以看出一些問題的。如唐前期河南和河東地區有水利工程46項,其中高宗武則天時期為15項,玄宗時期為11項。當然,工程有大有小,并不能簡單用數量來說明問題,但這些數字也可以告訴我們,高宗武則天時期,南方在漸漸興起水利工程的建設。如果隻拿開元、天寶這個時期進行比較,南方興修的水利工程數量并不少于同時期的北方。我們可以推測,當北方水利工程建設全盛時期,南方也在快速建設。
水利建設,對農業生産的影響極其重大。海塘的修築,從此可以使塘内的土地免遭鹹潮侵蝕,在淡水不斷沖刷下,大量的農田可以種植莊稼,墾田面積越來越大。在農業較快發展下,人口導入明顯,數量增加,從事農業和漁業者生活能夠得到保障。海塘對中唐以後江南農業開發意義十分重大。特别是廣德年間在太湖東南地區的嘉興屯田,出現了“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嘉禾一穰,江淮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為之儉”的局面,這與海塘修築密切相關。可以确定,中唐安史之亂後江南之所以能迅速成為國家重要的财賦之地,與玄宗年間一系列重要水利工程的修建密切相關。農業基礎打在開元年間,而成效顯現在廣德、大曆年間。
我們已經看到,唐代前期,江南農業生産已經有了相當高的發展水準。玄宗開元間,中原地區糧食缺口增大,江南糧食曾被大量運往北方。裴耀卿改革漕運後,三年間從江南運糧七百萬石。以後崔希逸為轉運使,每年轉運一百八十萬石。中唐以後,江南農業當然有着大步向前發展的事實,但開元天寶年間早已有了快速發展的态勢。
開元天寶年間,江南地區的手工業也已經有較高的水平,在不少行業上頗具特色,與同時期的北方手工業相比較,已難分伯仲。
以絲織業為例。現有史料記載的唐前期江南絲織業資料,大都是反映開元天寶年間的狀況。一是江南幾乎每個州都有絲織品的生産,二是江南有8州生産特殊絲織品。汪籛先生認為唐代前期主要絲織品區有三個,其中吳越是三者之一,當然他也指出江左的絲織品工妙猶不足與河北、巴蜀地區相比。唐代後期,江南絲織業有更快的發展,但這種較快速發展的基礎是在開元天寶年間奠定的。開天時期江南布紡織十分普及。《唐六典》卷二○“太府卿”對“諸州庸調及折租等物應送京者”進行了分等,其中江南的調布等級如下:第一等:潤州火麻;第二等:常州苎布;第三等:湖州苎布;第四等:蘇州、越州、杭州苎布;第五等:衢州、婺州苎布;第七等:台州、括州、睦州、溫州苎布。江南各州幾乎都有布作為貢和賦。
《通典》卷六《食貨典六·賦稅下》雲:“(開元二十五年令:)其江南諸州租,并回造納布。”又雲:“按天寶中天下計帳……課丁八百二十餘萬……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萬餘端。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從開元二十五年開始,江南大部分州租折納成布,轉漕至北方。在天寶計帳中,江南的丁數,約占全國總丁數的23.17%,是全國納布人數的42.2%,是全國輸布總量的55.07%。從這個數據而言,開元天寶年間江南經濟單就布這個手工業産品而言,在全國已經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全國一半的布是江南制造。
不難看出,正因為有了開元盛世時南方經濟的快速崛起,安史之亂後,南方經濟才能有力、快速地替代北方,大量糧食運向北方,成為“國用大半”的财賦的中心。所謂“辇越而衣,漕吳而食”局面的形成,沒有玄宗時期奠定的發展基礎,中唐以後是不可能會輕易地出現這樣的局面的。也就是說,開天盛世時期的南方,其實已經為國家财賦重心的轉移準備好了基礎條件,一旦北方陷入戰亂,南方在短時間内就能挺身而出,支持政府的财政費用。因此,安史亂後的财賦重心南移,既是偶然的,但同時也是曆史的必然。
開天盛世時期的江南,經濟發展十分快速,經濟發展水平已達到一定的高度。這是我們在談論開天盛世及江南經濟中唐以後的發展時,不能勿略的一點。

四、蘇、杭為什麼是天堂
唐五代時期,蘇州和杭州發展較快,在全國城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影響越來越大。唐末韋莊有《菩薩蠻》說:“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唐代人不斷用詩詞來描繪江南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優美,向往江南舒适的生活。至南宋範成大《吳郡志》引時人的一句諺語,更是令人大吃一驚:“天上天堂,地下蘇杭。”意思是指天上最美的是天堂,人間最美的是蘇杭。南宋人的眼裡,蘇州和杭州是江南最美麗、繁榮與富庶的兩個大城市。他們的觀點,其實是有依據的。因為宋朝人另有一句諺語說:“蘇湖熟,天下足。”當然幾個城市相比較,範成大認為“湖固不逮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蘇州在杭州前,兩個城市都遠超其他城市。
蘇州在唐五代江南城市中,是規模最大和商業經營最為活躍的城市,所謂“浙右列郡,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蘇州處于江南運河的中段,面臨太湖,北可出海,沿長江可到内地,被稱為“雄郡”,“東吳繁劇,首冠江淮”。蘇州城内商業經營十分繁盛,“複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市内商人雲集,“合沓臻水陸,骈阗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劉禹錫當刺史時,就說蘇州的賦稅,“首出諸郡”,綜合經濟實力為江南各州之首。白居易也說:“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杜牧說:“錢塘于江南。繁大雅亞吳郡。”意為蘇州第一,杭州第二。蘇州城内的人口達數十萬,特别是唐後期在一般城市人口下降的情況下,蘇州不降反升,大曆年間進升為江南唯一的雄州。因此範成大認為“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是江南區域内最主要的經濟中心城市。
杭州位于江南運河和錢塘江、浙東運河的交彙外,“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沖要之津”。唐代杭州的商業相當發達,人稱“東南名郡”,“咽喉吳越,勢雄江海”,“水牽卉服,陸控山夷,骈樯二十裡,開肆三萬室”,行商坐賈,熱鬧繁盛。中唐時期,杭州城内戶數已超過一萬,是個人口超過十萬的大城市。杭州是沿海的一個重要港口,從福建、嶺南、浙東來的商人都得通過杭州沿運河前往北方,“魚鹽大賈所來交會”,是“通商旅之寶貨”的重要貿易城市。司馬光感歎杭州的經濟發展較快,說錢鏐築捍海石塘後,“錢塘富庶,盛于東南”。特别是杭州在唐末五代成為吳越國的都城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成為東南地區的商貿中心。宋朝王明清《玉照新志》說:“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蘇、會稽二郡,因錢氏建國始盛。”如果說杭州在唐後期城市發展尚不及越州,但在錢氏建都後,其繁榮絕對是超過越州,與蘇州并起并坐。柳永《望海潮》說北宋初年的杭州是“東南形勝,三吳都會”,“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市列珠玑,戶盈羅绮,競豪奢”。而歐陽修的描繪更是把杭州說成是一個東南的商業大城市:“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霭之間,可謂盛矣。”
從這些古人的詩文描述中可知,蘇、杭兩州到唐五代至宋初,是江南最發達的城市。他們的發達具體來說在這樣四個方面比較明顯:
一是城市的商業比較發達,四方物資會聚。蘇州城内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前來經營的商客。劉禹錫有詩談到:“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樯多估客。”五代吳越國孫承祐請人吃飯,指着桌上的盤子對客人說:“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蝦魚,西之粟,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這并非是誇張用語,恰恰反映出杭州城的商業供應十分繁盛。
二是城市規模龐大,風景優美。蘇州城周四十二裡,而杭州在唐末五代多次修築後,城垣凡七十裡,是江南最大的城市。蘇州城内六十坊,河道縱橫,棋盤狀分布,十分規整,所道“水道脈分棹鱗次,裡闾棋布城冊方”。蘇州附郭縣吳縣和長洲縣各管三十坊,今六十坊名稱《吳地記》都保留了下來。蘇、杭都是環境特别優美的城市,曾擔任過兩州刺史的白居易寫下了很多贊美的詩。如談到蘇州:“吳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晚色萬家煙,秋聲八月樹。”談到杭州山水,他認為江南無出其右:“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又說:“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
三是城市人口衆多。吳融有詩雲:“姑蘇碧瓦十萬戶,中有樓台與歌舞。”陸廣微《吳地記》記載蘇州唐後期有戶十四萬三千多戶,扣除各縣的戶數,蘇州城内總人口推測在二十萬至三十萬之間。而杭州人口在成為吳越國首都後也是猛增。後周顯德五年(958)四月,杭州城内曾發生過一場大火災,“城南火延于内城,官府廬舍幾盡……被火毀者凡一萬七千餘家”。這場大火隻是燒毀了杭州城的南部,我們推測其時杭州的實際住戶最起碼在三萬戶以上,或許會達到四萬戶左右,因而城市總人口約在二十至二十七萬之間。
四是城市文化繁榮。由于大量園林修建,蘇杭兩州附近山水明秀,造就了城内人們遊玩之風盛行。如蘇州“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詩人李白、杜甫、顧況、杜牧等曾駐足蘇州,流連歌詠。杭州西湖是士女優遊娛樂之所,“綠藤蔭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是遊樂者的天堂。城市内文化活動豐富多彩,歌舞表演深受人們喜愛。張祜談到杭州的柘枝:“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蛾暫起來。紅罨畫衫纏腕出,碧排方胯背腰來。旁收拍拍金鈴擺,卻踏聲聲錦袎摧。看著遍頭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這種西域傳進的少數民族舞蹈,舞女跳時流波送盼,含情脈脈,是一種半脫衣舞。唐代城市正月十五日晚上一般都有放燈、觀燈的習俗。白居易《正月十五日夜月》談到杭州:“歲熟人心樂,朝遊複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裡,不合厭杭州。”而蘇州的正月十五晚:“十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妝。歌鐘喧夜更漏暗,羅绮滿街塵土香。”家家戶戶燈火通明,婦女們自由出外觀燈遊玩,穿上漂亮的衣服,成群結隊,信步遊走于燈海人潮之中。
白居易曾說:“杭土麗且康,蘇民富而庶。”杭州在中唐是以風景優美著稱,蘇州是以經濟上的富足傲立江南。杭州遠勝過浙東各州:“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蘇、杭兩城經濟繁榮、歌舞升平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南宋,平江府仍是江南運河上的重要城市,而杭州成了南宋的都城,城市發展更上一個層次。在這種情況下,時人談到杭州時說:“輕清秀麗,東南為甲;富兼華夷,餘杭又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宮也。”杭州被比喻成完美的地上天宮。杭州“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也”。談到蘇州時說:“吳下全盛時,衣冠所聚,士風笃厚”,“吳中自昔号繁盛,四郊無曠土,随高下悉為田”。這些都是共識,是大家公認的事實。

五、江南文明是中原江南化嗎
江南文明,是長江流域文明自身發展的産物。上世紀30年代以後,在江南多地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浪渚文化、崧澤文化、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江南文化古遺址不斷發現,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都說明,長江流域的文化是一種以種植水稻為主的稻作農業文化,與中原是屬于兩個不同類型的經濟生活體。總體上,史前時代,長江流域的文化雖然也有很高的水準,但發展水平慢于中原地區。不過這一時期的文化也與其他地區的史前文化發生了頻繁和密切的交流,如浪渚文化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而中原地區也發現有浪渚文化的遺物。
先秦時期,江南地區發展較為緩慢,人們斷發文身,信鬼占蔔,相傳泰伯、仲雍是從中原來到江南,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思想。春秋戰國時期,江南先後出現吳、越兩國,楚國的文化也曾傳入,比起同時期的中原文化,江南的發展是落後于北方的。秦漢時期,統一國家的政治中心在北方,江南地區雖然是國家的一部分,但發展與北方有一定的差距,其時國家的基本經濟區都是在中原地區。六朝時期,随着北方士族及普通百姓的大量流入,江南文化以其自身的特點向前發展着。北方帶到南方的先進生産技術和農業管理思想,都融入到南方的文化中。不過南方的發展自有特點,在一些社會制度和具體的措施上,南方優于北方,常會被北方人接受。從這一點上說,唐以前江南文明并不是簡單的中原江南化,而是江南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吸收各種文化包括北方中原文化的結果。
隋朝統一南朝後,随着有意識的消滅南北差異,江南文化與北方的差距在不斷縮小。江南經濟在唐前期發展很迅速,但總體實力不如北方。中原安史之亂後,唐政府努力将江南打造為國家的财賦中心,随着北人的南遷,北方精耕細作集約化式的農生生産方式傳到了南方,同時大力開墾荒地,使江南在國家财賦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就隋唐時期而言,唐前期北方經濟發展較快,江南雖也有不小發展,但速度尚及不上北方。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南方暢開胸懷接受了北方的生産技術和生産要求,而其時北方的發展幾乎停止不前,從這一點說,接受了北方思想的江南文明,在中唐以後發展變快,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
五代吳越和吳、南唐時期,江南地區不但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響,還同時接受外國和其他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入。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乃至非洲和中亞等一些國家,都與江南有着密切的商貿關系,同時又不斷輸出他們的文化,在江南産生一定的影響。一些北方的少數民族,如契丹等,越過北方的中原政權,與江南保持着密切的聯系。
北宋時期,江南在國家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尤其北宋滅亡,大量的北人南逃,很多士大夫都緊跟着皇室來了杭州附近,在嘉興、松江、蘇州等地紛紛定居,他們将北方的生活方式帶到南方,與南方傳統相結合,将南北文化融合,創造出了新的江南文化。很多望族世代在江南地區居住,具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比如松江府,大量的北人前來後,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南宋魏了翁說:“吳中族姓人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彬輩出。……而居華亭者為尤著。蓋其地負海忱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于所當事,故士奮于學,民興于仁,代生人才,以給時須。”就是說,華亭地區曆來就是士人大族居住的地方,由于這裡經濟比較發達,所以華亭士大夫最主要的特點是“奮于學,興于仁”,刻苦學習,講究仁義誠信,最後出了大量的人才,為社會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南來的士大夫大量修築文化意境的園林,玩賞山水、煙光,把酒弄詩,悠閑自得。宋元時期來到江南地區的官宦士子數量增多,他們不但對周圍産生了言傳身教的影響,而且很多士大夫意識到教育對一個地區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因而盡力協助官方興辦學校,傳播文化知識。大族世家一般都從小培養子弟讀書,走科舉登第的道路,從而進入仕途,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南宋末年至元初,仍有部分士人望族南遷,尋找生活的新機會。
從這些方面而言,江南文化是有獨特的發展軌迹,與中原文化并不完全一緻,但江南文化在前進的過程中與北方的中原文化是密切相關,江南文化深受中原的影響。江南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實際上就是南方傳統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結合體。
我認為唐五代人的“江南”概念在發生變化,有大、中、小幾種稱法,但總體上所指區域在越來越小,而指向兩浙地區為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江南人的社會風氣在兩漢時期是崇尚武藝的,但魏晉以後漸漸發生變化,至唐代以後,江南人崇尚儒術和教育,這其中變化的原因主要和北方士人大量南遷後重視教育、科舉和信仰宗教有關;蘇、杭兩州經五代至宋初,被人稱為天堂,其發展主要是在唐代中期以後,在城市商業、規模、人口、文化方面是當時最為繁華;江南文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但不是簡單的中原江南化堆積。
(本文收入《近代江南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12月。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有注釋,此處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