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賀(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文學副教授)
回顧即将結束的這一年的讀書生活,仍不得不讓人感歎“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不僅自己購買的許多書至今都還沒有讀,許多師友寄贈的大著、新刊同樣未能悉數拜讀完畢,要寫的文章、要修訂的幾部書稿也都沒有完成,隻能留待以後。因此,以下的片言隻語,雖立足于廁身的中國文學專業,不敢“跑野馬”,但也隻是一些個人初步的、粗淺的、對本年新出部分研究著作的閱讀感受,疏漏、悖謬、孟浪之處均所難免,敬請讀者諸君匡我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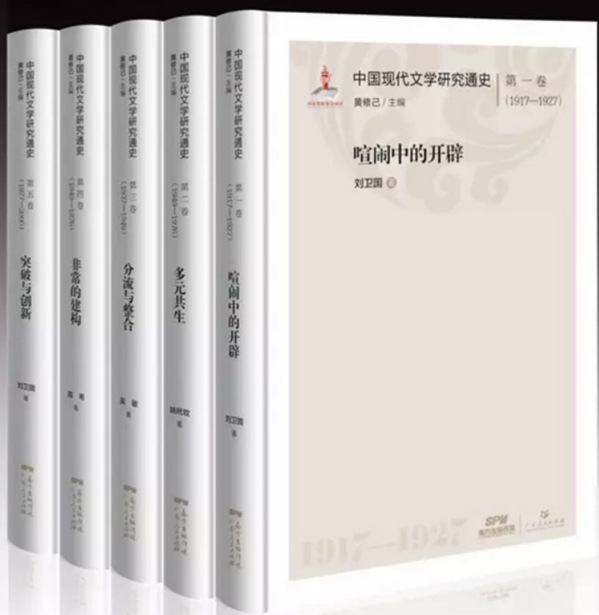
首先也許應該談到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黃修己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全書五大冊、一百多萬字,從五四新文學初創期一直寫到新世紀的研究進展,作者姚玳枚、陳希、吳敏、劉衛國,均為師從黃修己先生、學有所專的中青年學者。其實從《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及其修訂本,到兩卷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再到五卷本的《通史》,黃先生及其領導的學術團隊所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學科史的高度也正由此得以不斷确立。這套書問世後,我和中山大學的師友聯合舉辦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再出發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通史》在線對談會”,進一步較深入地讨論了其學術貢獻及有待發揮的地方,與會學者的精彩發言和會後同仁們的申論,即将或已經在不同刊物發表,此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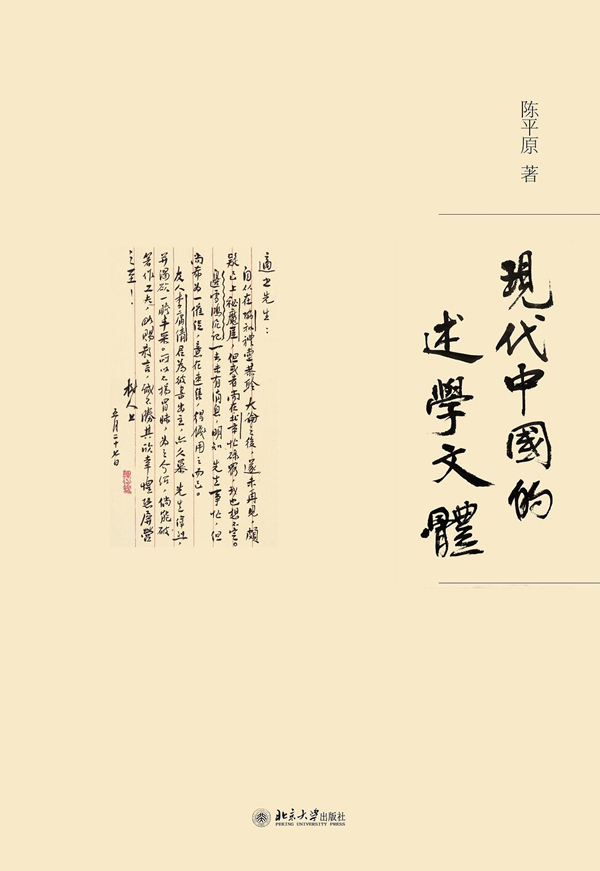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陳平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版)也是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的一部書。該書各章此前多已在學術刊物發表,早已拜讀過,但都為一編且改為專書體例之後,仍可見出作者對此問題思考的系統性、廣度和深度。事實上,從晚清至今,中國人文學者的著述體例與述學文體的變化、轉型尚未完成,今天我們仍能時常聽到諸如關于“西式論文”“西式規範”等是否适合中國人文學術的讨論,就此而言,無論是蔡元培、章太炎的文體意識,還是梁啟超、魯迅、胡适的學術文,這些現代學術先驅的思想遺産,對于今人如何确立言說的立場、方式與邊界,或都有一探再探的價值。此外,作者今年還出版了《遊俠·私學·人文:陳平原手稿集》(越生文化2020年3月版),内收其論文、著作、随筆、書信等手稿多篇。當代學人出版手稿者,坊間尚不多見,此書不僅印制精良,所選篇什也多能代表一代人的學術旨趣、精神氣質和立場追求,當然也有壓在紙背的“人間情懷”。尤其從家書這一較具私人性的手稿中,我們可以一窺其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治學、治生的不易,和面對不甚安定的外部環境時仍能葆持的一種樂觀、自信、深耕學術的心态。事實上,也正是在這種心态的驅使下,其先後貢獻出了《中國小說叙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等多種重要著述。

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研究愈益自覺,逐漸有分裂成為一專門學問領域的趨勢。《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十講》(陳子善著,複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版)的出版,為此一領域的代表性作品。作者治現代文學文獻史料有年,著述等身,是次應複旦大學出版社“名家專題精講”叢書邀請,将曆年所作重要文章,按作品版本研究、集外文和輯佚、手稿、筆名考定、書信、日記、文學刊物和文學廣告、文學社團史實探究、作家文學活動考略、現代文學文獻中的音樂和美術十個方面,加以遴選,試以不同例證、不同個案的研究揭示此一領域研究的堂奧,凸顯“實踐性”優先于理論生産的重要,足稱金針度人。在其近兩年出版的《說郁達夫》《說徐志摩》《梅川序跋》等書中,作者也相繼提出了發展“徐志摩文獻學”“張愛玲文獻學”等現代文學文獻學分支之分支的設想,可見其對文獻研究體系、理論方法的思考雖未結撰成專論發表,但仍在持續進行之中,且有相當激進的一面,不可不察。另外,今年秋天我也編輯了一冊《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陳子善教授榮休紀念集》(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20年9月版),對這方面問題感興趣的讀者,或可一并參考。

另一部值得一提的著作是《重溯新文學精神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學術因素》(李振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版)。該書采用“内爍型”的研究思路,細細爬梳新文學傳統與晚清學術思想史的關系,所見極為深刻。其中更不乏研究者強烈的主體性和當代意識,是一種有抱負、有情懷、有現實針對性的學術。當然,藉此我們也許還可以讨論思想史研究的不同思路、晚清的學術思想和晚清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新文學的獨創性品格究竟為何、如何看待不同于危機時刻的學術想象的“純學術”、如何看待新世紀以來本書未征引相關著作的研究等一系列問題。此書出版後,友人金理教授組織了一次讨論會,我們的發言也将于近期集中公開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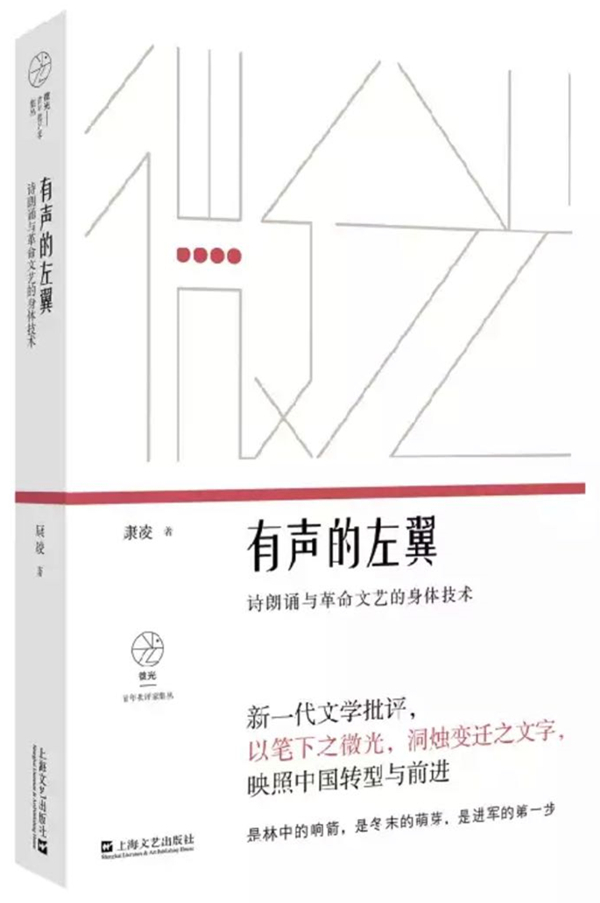
本年除了上述這些資深學者仍在持續貢獻新作,中青年學者的大著仍出不少,其中不少都是相熟的師友,多有駁诘往複,無須辭費。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有聲的左翼:詩朗誦與革命文藝的身體技術》(康淩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6月版)。這本書有意思的地方,不僅是從聽覺文化的角度研究左翼文學、文化,而是研究左翼文學、文化,卻沒有被既有的左翼研究思路框住、拐跑,相反,揚榷而陳之,是從一種新的批判性的角度出發,重新審視了1930年代左翼詩歌對音響形式的經營和其中内蘊着的感官動員技術。換句話說,作者研究左翼,但他的立場不是左翼的,他的思想預設、出發點和最終想要解決的問題也并不是要重新回歸左翼(當然也不是非此即彼,倒向新自由主義),更不是想要維護某種絕對主義的運思方式和自以為真理在握、在道德和審美立場上處于強勢地位的論述策略,而是為了拓寬左翼文學的诠釋空間。但站在充分的後設的立場上,如何看待朗誦詩等左翼文學的“文學性”(難道僅是一個特殊的認知裝置?或流行的“文化政治”概念就可以取代、解釋?),這一問題仍懸而未決,特别是在教學、文化傳習中,一首滿坑滿谷戰鬥口号的詩歌、一篇寫生産隊挖地開荒的報道文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文系之外的讀者所接受?又能夠流傳多久?何以證明其豐富的“生産性”不是一套特定的學術話語(意識形态)、慣習的自我建構和不斷增殖的過程?這些問題似仍值得深入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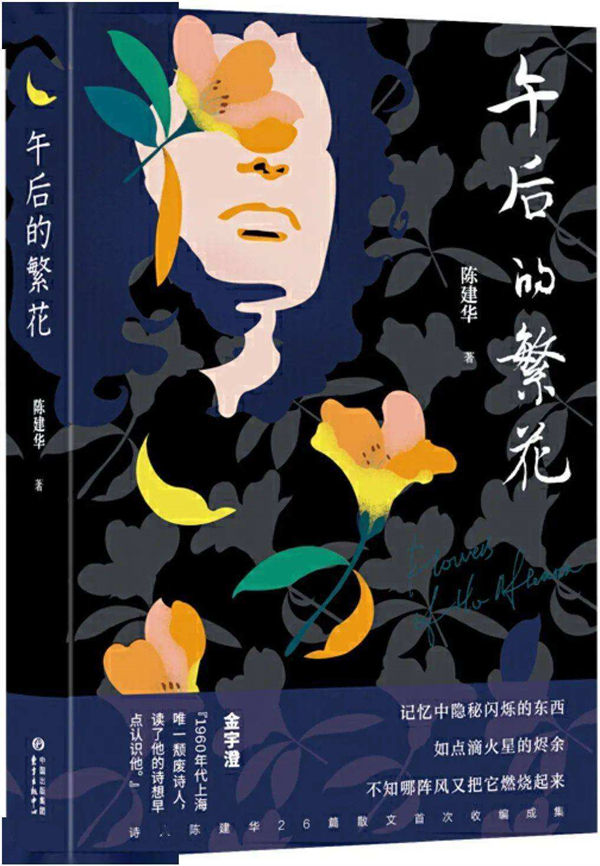
專書之外,幾種新出的關于近現代文學、曆史、電影、藝術的随筆集也很可一說。《午後的繁花》(陳建華著,東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版)中,所收不僅有其近年新撰如《文以載車》《陸小曼·1927·上海》等佳作,也有首次結集出版的二十餘篇散文和學術随筆。但無論是對民國電影史的重探,還是對清末民初文學與思想的重訪、物質文化研究、視覺文化研究等,抑或是關于新世紀一度流行的“狼文化”的批判,乃至其追憶師從李歐梵先生及紐約讀書經曆等等,都帶着“老克勒”不懈探尋“詩與真”的明顯标記,這些“記憶中隐秘閃爍的東西/如點滴火星的燼餘”,見證了學者之外作為詩人、作家的陳建華的另一面相。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再讀《陳建華詩選》及作者其餘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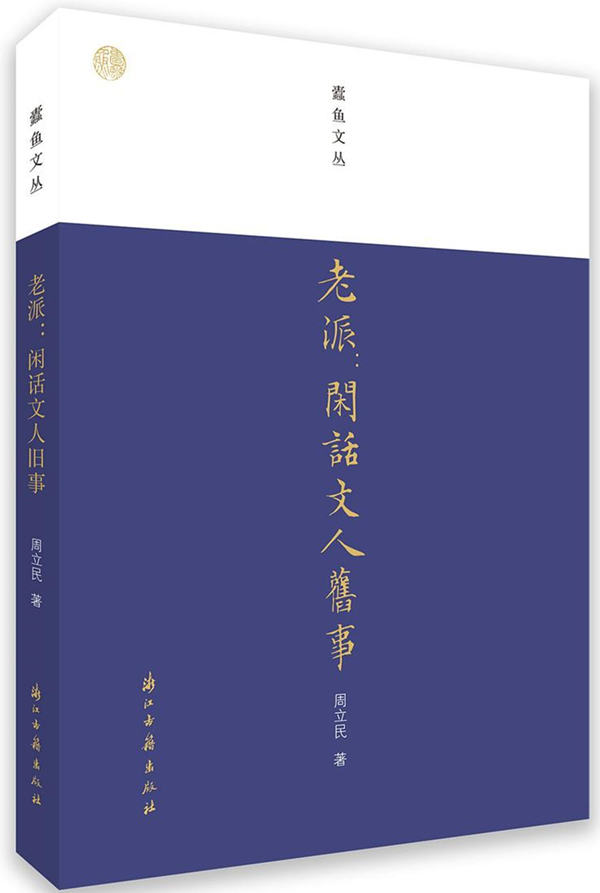
《老派:閑話文人舊事》(周立民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版)《星水微茫駝鈴遠》(周立民著,商務印書館2020年7月版)是作者在《傳記文學》等處的專欄文章、随筆、讀書筆記的集合。前者各篇篇幅較短,後者諸章論述更從容,但無一例外體現出作者因接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兼以勤于讀書、敏于思考,雖是論文述史卻不偏執一端、筆端仍飽含感情等鮮明特點。在其附錄的《從“不好看”說起——學術期刊與學術文體》一文中,作者透過對當前學術期刊論文尤其“學報體”的批判,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研究、寫作信念,乃是企圖恢複人文學術寫作的多元性,試驗其間存在的多種可能,于我心有戚戚,而這一點不僅對于某種程度上已經僵化了的當代學術文體的革新具有警示意義,也再一次在事實上回應了陳平原的相關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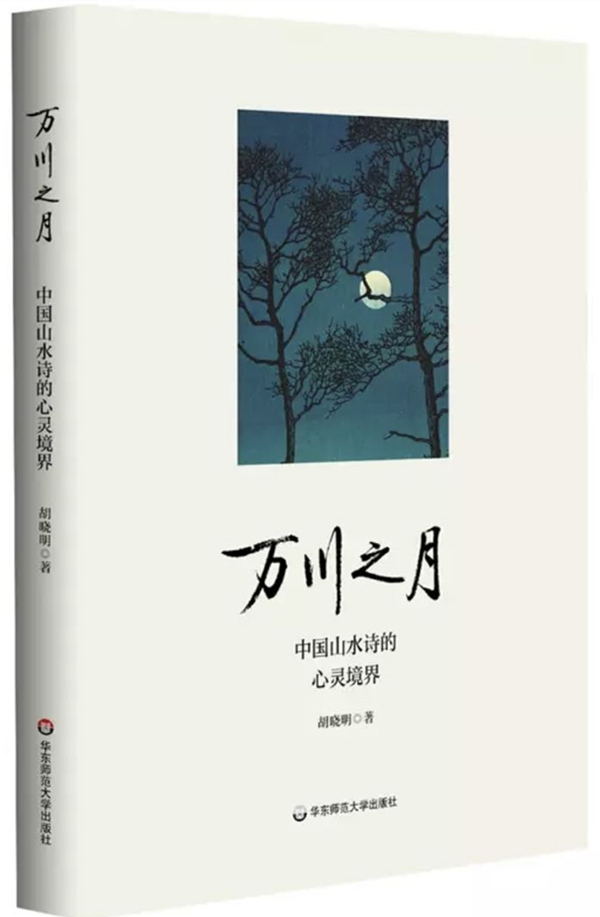
古典文學的書今年讀得不多,印象比較深的有兩種。一種是《萬川之月:中國山水詩的心靈境界》(胡曉明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版)。這是作者的名著,曾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版,新世紀初期又出過一版,今年又出一新版。全書認為山水詩“是中國哲學精神的感性顯現,除了表達詩人的心境,更是表達着中國詩人代代相承的共通的心境,集體的意欲;這共通的心境與意欲,正映射着中國哲學的真正性靈”。因此,山水詩就不能僅僅被看作“精妙優美的語言文字或風景畫”,還應探究其中“所表現的中國文化的心靈境界”,發現其中“隐藏在技法、家數、淵源、流派以及風格背後的共通的民族文化的詩心”。因此從雪夜人歸、啼鳥處處、花淚蝶夢、荒天古木等十個方面,依次論述山水詩中映現出的生命的漂泊與安頓、悲哀與複蘇、有我與無我、荒寒與幽寂等主題。但作者的論述并不是純理論的空轉,而是建立在對兩百餘首山水詩作的細緻賞析與精妙解讀之上,也很好地平衡了對詩歌文本的細部論述與對中國山水詩及其哲學、美學意涵的整體理解,從中不難見出作者重建後五四時代中國文論的努力。例如這樣的一段論述——
“山水詩滿足什麼樣的心理欲求呢?隻要看中國古代山水詩中,有那麼多的甯靜安谧的村莊、田園、古刹,隻要再看看最早的山水詩,其實是對不自由人生的一種逃避,我們不妨認為山水詩是一個最大的補償意象(compensatory image),盡管詩人們的真實命運中,充滿了颠沛流離和不安焦慮的因素,他們對山水的崇尚心理,紮根于一種對更自由、更永恒、更真實的人生形式的持久的精神追求之中。宋人有兩句詩:‘水隔淡煙修竹寺,路經疏雨落花村。’(楊徽之《寒食寄鄭起侍郎》)其實,每一個中國詩人的心靈深處,都有一處隔水相望的‘淡煙修竹寺’與‘疏雨落花村’。盡管山水詩語言、風格有各種變化,但其中所代表的那一份普遍的精神需求,卻絕不會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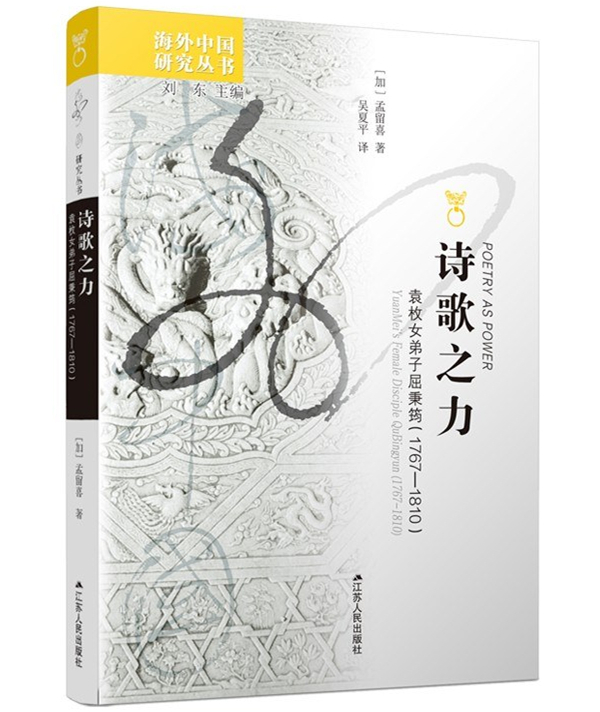
另一種是《詩歌之力:袁枚女弟子屈秉筠(1767-1810)》(孟留喜著,吳夏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版)。這本書從表面上看,寫法比較傳統,自為袁枚得意女棣屈秉筠編纂年譜始,至訂成袁枚所有女弟子年表結穴,依次讨論了屈秉筠的時代、家鄉及家庭背景,社交網絡,理論主張及兩類代表性詩歌(家庭詩和關系詩)的創作特色等面向,有點不太像是一般我們想象的“海外漢學”,但在具體的論述、分析中,仍不乏洞見。如在分析其家庭背景時,提出了“家庭變成文學之網”這一重要觀察,讓我們想到近現代文學史上的張氏三姐妹、林徽因和邵洵美的客廳、上海馬斯南路曾樸的文藝沙龍、北京慈慧胡同朱光潛宅的讀詩會……評析其理論主張時,則發現屈秉筠的家庭文學圈和包括袁枚女弟子在内的虞山圈的存在,已顯示出一個因詩歌傳播而締結的“女性詩歌評論共同體”;由此體現出的所謂的“詩歌之力”或“女性詩歌之力”,從理論角度看,乃是女性生活、體驗構成其藝術實踐之動力,具體而言,正在于屈詩“使複雜的家庭關系簡單化,使周邊所有人和她的聯系更加緊密……也使其本人受到本地區内外的人的廣泛的仰慕。”
盡管這一研究結論可能并不驚人,但對于我們如何研究一位不甚知名的作家的生平著述,這本書仍能予人很大啟發,也再一次向我們給出了一個不同于何炳棣“做第一流學問”的思考方向:或許并無二三流的選題,隻有二三流的研究。也正如在藝文創作中,“怎麼寫”遠遠比“寫什麼”要重要。
鍊接地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330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