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恒 | 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原載《探索與争鳴》2020年第9期
非經注明,圖片來自網絡

陳恒教授
知識是人類認知的成果,它“是曆史地成長起來的,是無數人類個體的各種文化活動的結晶物”。知識借助一定的語言形式,或物化為某種勞動産品的形式,可以交流和傳遞給下一代,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财富。曆史知識就是這種意義上所發生的曆史事件給人們帶來的認知,這種認知有助于诠釋證據,它永遠涉及時間、時間的間距,即此刻的某個時間與往昔的某個時間的距離,并試圖探尋其中的意義。圍繞這一主題,筆者試圖探尋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曆史知識在人類知識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第二,形形色色的世界史理論背後都有價值追求嗎?第三, 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曆史學家?
曆史知識在人類知識中的地位
農業經濟時代後期,歐洲每年出版圖書約1000種,一個世紀才出版約10萬種;工業經濟時代,歐洲每年出版圖書超過10萬種。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出現在17世紀60年代,1750年世界上隻有10種期刊;而在工業經濟時代,大約每過10年,科技期刊數量便增加10倍。有人估計人類知識總量在工業經濟時代每10年翻一番,在知識經濟時代則每5年翻一番。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後的30年間,全世界發表的論文數量超過了此前曆史上的總和。但是,曆史知識在人類知識中所占比重卻呈下滑趨勢。當前中國大陸各類雜志有近萬種,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組織評定的CSSCI來源學術期刊567種,其中曆史類僅30種,曆史學類學術雜志比例并不高。
為什麼曆史知識在人類知識中分量越來越少?曆史學家對決策的影響似乎越來越小,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總體來看,在人類文明早期,曆史著作尤其受重視,滿足了彼時人類的好奇心。到曆史學專業化、職業化的19世紀,可以說達到了影響力的頂峰。而到20世紀,曆史學在人類社會中的影響,無論是從知識生産的角度,抑或是曆史知識對人類解決問題的實用角度,還是從對政治的影響來看,都呈現出下降趨勢。當下的專業史學家之所以感覺曆史學還很重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專業愛好造成的誤解,隻是一種自我感覺。不可回避的事實是,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曆史學的作用越來越小,但并不是曆史學不重要了,而是說傳統意義上的曆史著述已經被學科分類越來越細化的其他知識領域取代了,曆史著述的表述也越來越蘊涵着某種價值取向,且越來越與意識形态相關了。
形形色色的世界史都有其價值寄托
世界曆史(world history)這個術語從來都不是一個有穩定指示對象的示意詞。它含有多種不同名稱的語義和分析模式,其中一些以其悠久的學術傳統為榮,另一些則僅在最近時期才得到明确認同。這些名稱包括普遍史、比較史、全球史、大曆史、跨國史、聯系史、交織史、分享史以及其他一些名稱。世界曆史與所有這些名稱不同程度地交疊在一起。
世界曆史名稱的變化不僅反映着時代的變遷,更折射時代的趣味、精神與價值。民族的、國家的、區域的、世界的,它們的曆史都受民族記憶與時代需要驅動。近代以前各民族的“世界史”在一定意義上都是區域史,超過特定邊界的曆史記述基本都是一種曆史的想象,不具有學術性。但地理大發現之後,這一切都改變了。文藝複興以來西方世界不乏各種世界史理論,普遍史、世界曆史、現代化理論、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世界體系理論、依附理論、全球史等,都可以納入世界史的範疇,這些都是曆史學家為解釋所屬時代現象而提出的理論方案。
如果不考慮古典作家希羅多德、波裡比阿、西西裡的狄奧多洛斯,以及奧古斯丁、伊斯蘭世界的伊本·赫勒敦等人的著作,在歐洲,自博叙埃的《論普遍史》(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1681)起,各種世界史編撰層出不窮,試圖證明曆史是線性發展的、不斷進步的,是上帝意志的不斷呈現。法國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杜爾哥說:普遍史包含對人類一系列進步的思考和對引起這些進步的原因的仔細探究。随着時間流逝,新的民族出現了。在各民族不均衡的進步過程中,被野蠻人包圍的文明民族正在征服或已經征服了他們,并同他們混居在一起。無論後者是否受到前者的藝術和法律的影響,也無論征服者是否使蠻力屈服于理性和文化的帝國,野蠻的範圍都在逐步縮小。啟蒙時代的伏爾泰撰寫《風俗論》對這種神學史觀進行猛烈抨擊,對後世的世界史研究産生很大影響。“在歐洲的啟蒙時代, 伏爾泰、孟德斯鸠和萊布尼茲都努力去了解波斯和中國的曆史與文化傳統, 并且嘗試着把它們融進更廣闊的世界史視野中。”美國政治哲學家沃格林指出:“全面解釋人類社會和人類曆史”的觀念在1700年以前并不存在,而對新世界的适應和進一步接觸亞洲文化将成為創造這種觀念的一部分。從此曆史學逐漸邁向職業化、專業化,湧現出一批偉大的曆史學家,在19世紀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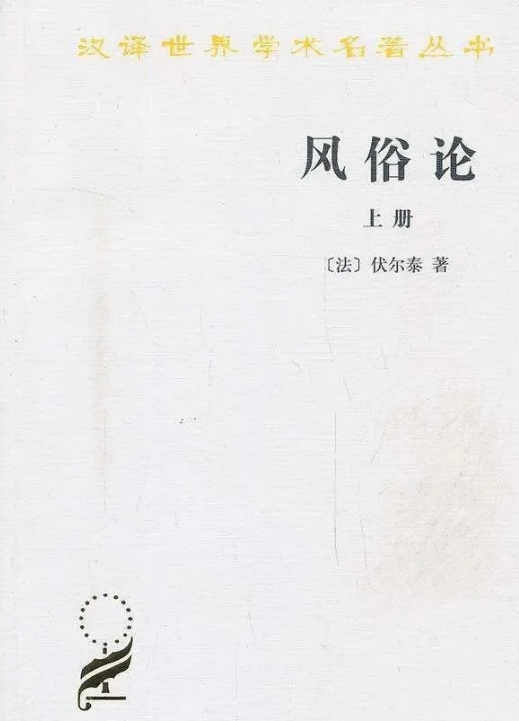
伏爾泰《風俗論》
偉大曆史學家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善于解釋往昔世界,回應人類的各種問題。麥考萊、卡萊爾的浪漫主義史學,蘭克學派的客觀主義史學,巴克爾、泰納的實證主義史學,德羅伊森的曆史主義史學,其他如曆史的輝格解釋、作為文明的曆史、自下而上的曆史等,無不試圖構建世界曆史的解釋體系,無不借助曆史學為政府服務,無不擁有自己的理想寄托。柏林大學的特賴奇克(Heinrich Treitschke,1834—1896)認為,支持祖國就是他寫作和教學的動力,他美化德國戰争行為的演講得到學生和軍官的歡呼:沒有戰争就沒有國家。我們所知的一切都出自戰争,由武裝力量來保護國家公民仍是其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務。因此,隻要存在多個國家,戰争就會持續到曆史的終結。布羅代爾在地中海世界三部曲中明确認為西方的曆史學是為國家服務的:“歐洲在發明了曆史學家的職業後,便用曆史學家為自己效力。歐洲自己的來龍去脈既已弄清,就随時準備提供證據和提要求。”
就已經出現的各類世界史而言,能影響一時的世界史都是“世界”帝國的曆史學家書寫的曆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種權力主要掌握在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手中,“二戰”後就逐漸讓渡給美國了,成為傳播美國文明的一種工具。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曆史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學術烏托邦,是高貴的夢想、彼岸的真理。
可以說,“二戰”以前的世界史著述都是進步主義觀念下的産物,不過這種觀念随着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破滅了。帶有目的論的進步史觀逐漸被取代了,新史觀重視“社會空間”而非“民族國家”,強調人類的“互動”“過程”、一個随時間推移而持續變遷的過程,這個過程最初在不同的地區而經曆不同,但最終把全球各地的民族及其傳統聯系起來。這是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恩格斯指出:“18世紀是人類從基督教造成的那種分裂渙散的狀态中聯合起來、聚集起來的世紀;這是人類在走上自我認識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在曆史學方面情況也完全一樣;這時我們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編纂著作,它們固然還缺乏評介并且完全沒有哲學上的分析,但畢竟不是從前那種受時間地點限制的曆史片斷,而是通史了。”當下的關鍵是中國史學界能提供什麼樣的世界史解釋理論、解釋體系、解釋框架。
解釋權就是文明發展程度的标尺,就是文化的定價權。我們能否獲得解釋權,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解釋權,我們的解釋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别人自願接受與信服,這是文化軟實力的真正表現、大國的内在本質。可見,衡量一國曆史學是否發達、是否有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能培養出多少能構建曆史解釋體系的曆史學家、有思想的曆史學家、有世界眼光的曆史學家。

恩格斯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曆史學家
有什麼樣的曆史學家就會有什麼樣的曆史作品,也就會塑造出什麼樣的國民品質,因此曆史學家的責任與使命是極其重要的。曆史在可見的未來仍難以擺脫民族—國家這一思維模式。曆史發展總是螺旋式的反複,比如在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大家都對全球化充滿信心,人流、物流、财流、智慧流等都暢通無阻,全球化勢不可擋,但瘟疫突然使這一切凝固了,似乎一夜之間又回到了19世紀的民族-國家時代。世界史編撰似乎也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官方強調大曆史,進行宏大叙事;學術界強調精細研究,越來越關注細枝末節,步入所謂曆史的碎片化研究。這是因不同的旨趣造成的,作為叙述的曆史與作為過去的曆史、作為想象的曆史與作為真實的曆史、作為政治工具的曆史與作為學術理想的曆史,兩者之間一直存在巨大張力。19世紀的德羅伊森為普魯士霸權找到亞曆山大這一偉人,創造出希臘化時代這一獨特概念,進行宏大叙事,目的在于為德國統一尋找曆史依據。康有為“托古改制”又何嘗不是如此。曆史上出現的各種考據派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碎片化研究,都是當時社會環境的産物。兩者都有其價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有其自身的知識體系,但近代以來中國學術浸潤在西方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之中,傳統文化知識體系遭到瓦解。史學也不例外,我們今天的曆史編撰手段、文本呈現形式、研究對象、研究範圍等都迥異于中國傳統史學。曆史研究的空間、時間、領域都發生了極大變化,很多研究領域還缺乏學術積累,且新的研究領域層出不窮,諸如空間史、情感史、動物史等。曆史研究的邊界、内涵、對象、方法在不斷演變,但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培養真正偉大的曆史學家。偉大的曆史學家不僅能夠真實呈現某個時空範圍内的人類曆史,其研究成果也深刻影響着人們的觀念和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類曆史。因此,假如對古今中外的曆史學家進行全盤檢視,對他們的影響力在廣度和深度上進行比較,從而評定級别和段位,就可以從個體曆史學家的角度反思曆史學在人類整體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問題。
那些在世界範圍内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曆史學家,其著作和思想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文化财富,如司馬遷、希羅多德,屬于A級。具有跨國家、跨地區和跨文化影響力的曆史學家,其著作涉及範圍一般也超越所屬國家和區域,如波裡比阿、普魯塔克,屬于B級。很好地記載和呈現本國、本民族曆史的曆史學家,對本國和本民族的曆史文化認同産生重要塑造作用,如李維,屬于C級。在史學領域有重要成就的曆史學家,其著作和理論推動某一研究方向的發展,如維拉莫維茲,屬于D級。還可以把一些産生不良影響的曆史學家、曆史著作列為E級。如果按照上述規則審視世界各國曆史學,按照得分多少來排列曆史學家、曆史學的影響力,然後再按民族國别計算其所占百分比,大體上就可看出各個民族國家在史學上的大緻貢獻。外國學者想知道中國人基于民族心理和意識形态的獨立的思考内容,曆史學是其理解中國的主要途徑之一;同樣,我們也需要理解外國的曆史意識是如何建構的,在整個國家的文化建構中曆史起着多大的作用。

當代中國曆史學研究體系建設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這個問題本質上是要解決中國曆史學與世界學術體系對接的問題。我們構建三大體系,不是搞一套别人看不懂的、有悖世界學術潮流的體系,不是關起門來搞學術建設,而是學習世界學術、融入世界學術、貢獻世界學術,從而彰顯自身實力的過程。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很難對接國際史壇,也很難和國外有影響的史家真正對話,會陷入自說自話的困境。職業曆史學家的任務與擔當是純學術研究,提出重新觀察世界、解釋世界、理解世界的理論與方法,盡快縮短與世界學術前沿的差距。一言以蔽之,為國家培養什麼樣的曆史學家,如何培養曆史學家,培養多少曆史學家,不但要結合現實需要,也要參考以往曆史學發展的經驗教訓。
來看一組現實的數據。2019年全國曆史學專業(060101)在校本科生為83687人(包括五屆學生,含2019年畢業數)。2019年全國曆史學專業招生實際報到人數為16774人。研究生培養方面,2019年我國已經擁有31個世界史一級學科博士點,80多個世界史一級學科碩士點,幾十個世界史博士後流動站,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養機制。曆史門類研究生總數,2019年是6502人(包含普通高校和科研機構),其中博士生1154人,碩士生5348人。2019屆全國高校畢業生人數達834萬人,再創近10年新高,其中曆史類畢業生占總數0.18%左右。可以發現,大多數高校曆史類專業學生畢業後并不從事與曆史學相關的職業,真正從事專業研究的不多。
由此我們需要思考:每年培養的這些專門史學人才能成為傳播曆史文化認同的主體嗎?或者說民衆的曆史知識、曆史意識由誰主導?是由這些曆史專業的畢業生主導嗎?未來30年我們能培養出大量的國際史學人才嗎?我們的培養機制能夠支撐國際史學人才的培養嗎?中國曆史學家何時能真正成為世界曆史學術的中流砥柱?
此外,要有學科自知之明,要抛棄本位主義,認清現實。曆史學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了,文化的多元早就肢解了先前的曆史學領域,不要高估曆史學家的作用,但也不能妄自菲薄。不能以傳統的思維理解什麼是曆史,真正的大曆史是包括各門人文社會科學的“大”曆史。
曆史不僅是通過過去來把握我們當下的民族、社會、文化,而且有時可以撬開封閉的思想,啟發我們的思維。但我們也不能期望過多。曆史不能保證寬容,盡管它被看作智慧武器;曆史不能保證常識,盡管它被看作知識之源;曆史不能阻止人類的驕傲自滿,盡管曆史充滿着經驗教訓……曆史必須時常進行改寫,盡管隻存在一個真實的曆史。曆史在未來可預見的很長時間内都将是民族-國家的曆史,盡管人們在不斷倡導跨越民族、國家、區域、文明的曆史,追求曆史的國際化,但這将是漫長的學術探究,“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曆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曆史的時代性、國家性、民族性在可見的未來是難以改變的。因此,我們需要自己的曆史,需要由自己撰寫的曆史,需要由自己的觀念體系、解釋體系、道德體系支撐起來的世界曆史。
鍊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MjcxMDEwNQ==&mid=2686278173&idx=1&sn=72201593713ff1dc430b70b7d6174805&chksm=ba68612b8d1fe83deb869df0475dd62f71cd312801a395742357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