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動态】
作者:陳恒(上海師範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
2016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創辦了《人文史》(History of Humanities)雜志,主編倫斯·波多在發刊詞中表明了其創辦雜志的緣起與目的:“我們懷着希望之情出版了第一期《人文史》。我們的期刊是基于如下事實出版的……人文學科對由學者、思想家和專家們編織了數千年的複雜知識網絡的重要貢獻沒有得到足夠的認識,其作用也被低估了。我們意在糾正存在于人類探索知識曆史中的這一不平衡現象。我們相信,一個更為平衡的圖景會告訴我們人類獲得知識的途徑是複雜的、多變的,而且是不可預測的,并往往涉及研究方法和視角在不同領域間的傳播。”
可以看出,創辦者的目的是要系統地梳理人文知識譜系。為什麼西方學術界會在此時出現“人文史”這樣一個研究領域?這裡所指的“人文”概念是什麼?人文史又包含哪些内容?人文史興起之前西方人文學科的發展曆程大緻如何?人文史的興起和數字時代之間存在什麼聯系?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概要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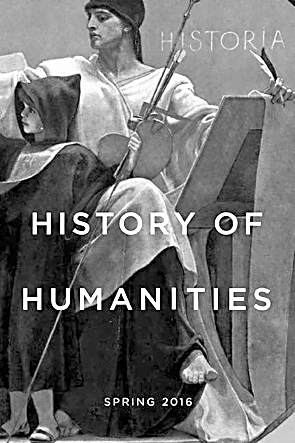
《人文史》雜志封面圖
什麼是人文
humanities(人文)一詞來自拉丁語humanitas,該詞相當于希臘語中的paideia(教化)。伊索克拉底宣稱:“我們所稱的希臘人是paideia(教化)上的一緻,不是血統上的一緻。”paideia(教化)是每一個希臘人都必須接受的文化教育。古代教育史權威法國古典學家馬魯(Henri-Irne Marrou,1904-1977)認為,paideia(教化)就是不論希臘人在哪裡安家落戶……他們首要的任務是建立他們自己的機構,他們的教育設施——初級學校和體育館。就是這些學校和體育館教授那些希臘人、非希臘人如何像希臘貴族一樣生活。這種教育方式是希臘式生活的入門,它造就了一批精英人物,而這些精英又在方方面面影響了民衆。可以說,paideia(教化)成為聯系希臘世界強有力的紐帶。這種觀念為後來的羅馬人所繼承,且随着羅馬人在地中海世界開疆拓土而傳播到各地。現代英語humanities繼承了paideia一詞的含義,表示“人類、人性、人道”,後來延伸為語言文學之意,也表示人文學科(通常包括語言、文學、哲學、美術、曆史等),總之是有關人類及其精神追求的概念。
伴随古典世界的衰落,宗教信仰文化逐漸取代世俗古典文化占據了人們的思想、行為領域,但到文藝複興時代,以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薩盧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等人為代表的人文主義者在歐洲各地尋找古典作家作品,這是歐洲自古典世界衰落後第一次有人整體上将希臘著作引入西歐,其代表性事件是1395年薩盧塔蒂邀請拜占庭學者赫裡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約1355-1415年)到佛羅倫薩講授希臘語,後者把荷馬、柏拉圖的著作翻譯成拉丁語,也培養了諸如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布魯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等一批知名學者。正是薩盧塔蒂扭轉了人們隻關注神學與聖經研究的局面,從而讓人們更加關注世俗曆史、詩學、修辭、語法以及道德哲學研究等。從這個意義來講,薩盧塔蒂是古典世界衰落以後人文研究的點火者。西歐世界自此以後進行了系統的世俗研究。意大利語言學家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于1440年寫成的《君士坦丁贈禮的證僞》開創了文本研究方法,證明《君士坦丁贈禮》系僞造文件,充分證明了人文的學術價值。培根于1605年出版了《學術的進步》,要求人們脫離經院哲學,主張全面改造人類知識。1725年,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新科學》中“發現真正的荷馬”,開創了把作品與時代背景、作者生平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方法,人文研究自此呈現出自身的特色。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則認為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對象,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都是完全不同的,從而把二者徹底分開。
什麼是人文史
人文史是研究人類認知的一門學問,不僅研究世界各種文化傳統如何産生、發展、傳播,研究這一傳統的當下現實意義,而且還研究各人文學科的産生、發展史,研究它們的學科體系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進入大學課程的。通過研究人文史,我們可以發現人是如何追求其精神世界,如何通過各種手段來表達其精神世界,又是如何反思精神世界本質的。一言蔽之,這是一部人類精神的表達、展現史。
作為精神表達史的人文史是知識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視人類過去所發生的一切行為為曆史的話,那麼這種人文史就是放大版的“史學史”,是一種獨特的學術史,不僅從宏觀的角度研究人文學科總體發展,而且注重研究各人文學科的社會經濟政治背景。人文史涉及的領域有傳統的視覺藝術(繪畫、雕塑、馬賽克、書法、碑銘、建築、攝影、電影等)、表演藝術(巫術、舞蹈、音樂、戲劇等)、文學藝術(詩歌、散文、小說、修辭、邏輯等)以及具有反思特色的宗教、曆史、哲學等學科,還包括一些新興學科,如媒介研究、數字人文以及曾中斷的古物研究等。這些精神領域都是人類自身的産物,都有一個形成、發展的過程。
人文史(人與精神的聯系)既不同于科學史(人與自然的聯系),也不同于社會史(人與社會的聯系),它在當代社會中與自然、社會成鼎足之勢,但這并不是說三者之間是割裂的、互不往來的,人文史在強調其自身的獨特性時,也強調與自然、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此外,人文史還探究真理是什麼,過去的意義是什麼,以及“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這類問題。
人文史興起的背景
人類精神經驗越是豐富,越是熟練地掌握精神表達模式,人類的創造力就越強大,思想就越深邃,受惠的群體也會越來越多,因此,學習人文史既是個體發展所必需,也是人類整體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文史教導我們如何理解傳統,如何在當下有效地言說。
從學科發展看,各學科發展史研究的不平衡使得加強那些諸如考古學史、宗教學史之類薄弱學科的學術史研究成為必要。當今被稱為“人文學科”的學術實踐已經成為人類認知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一過程始于人類試圖進一步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求知欲。這段漫長的曆史已采用一些成果豐富和頗具啟發性的方法加以研究,諸如曆史主義方法、比較方法、思辨方法,但這些方法的運用重點都集中于個别的人文學科研究領域,如史學史、文學史、語言學等,而在諸如學科産生史、學術交流史等領域卻付之阙如,亟須改變這種狀況。
從技術手段看,數字人文時代的降臨,徹底改變了研究者先前獲取文獻的路徑與方法,在根本上改變了知識生産的進程。數字時代所帶來的新視野不斷拓展當代研究者的想象力與研究領域。比如,就西方世界而言,把知識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審視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發展起來的事情,因為這一領域涉及衆多民族、語言、宗教與文化,時空範圍極其廣泛,研究困難重重,随着互聯網的出現,大量信息得以集中處理,才使這些困難逐漸消解。
從研究方法看,跨學科互動研究使很多研究領域出現新氣象,也出現很多新的研究領域,而經濟全球化更促進了這一趨勢。這些新方法極大地改寫了先前的研究成果,比如DNA技術的使用,可以對古代遺物進行複雜的分析,得出的數據是前人無法想象的。
從現實需要看,一方面,商業文化濃厚、功利化取向明顯、缺乏對社會自身進行反省等現象使得人文主義危機不斷存在于現實之中,而這種情況正是那些相信人文學科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人所擔心的,從而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使人文主義不斷得到張揚。另一方面,為追求眼下的經濟利益,歐美政府在不斷削減各大學人文學科的預算,學習人文學科的人數也在不斷下降,資金減少所帶來的壓力使“人文共和國”的團結意識陡增,使得人文研究者特别要加強人文學科在學術界的地位與話語權。
諸如此類的種種因素都促使人文學者團結起來,把人文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審視。人文史既是博雅教育的基礎與起點,也是一種知識體系,涉及時空廣泛,學科本身呈現出一定的模糊性,其所包含的各人文學科之間交互影響明顯,不同文化圈之間的交往所引起的相互借鑒也存在明顯的價值取向。當代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不少人缺少了自我關懷,輕視了人的尊嚴、價值與精神追求;新世紀的多元文化使得傳統的人文失去了先前的優勢;人工智能已經走出實驗室,大有取代人類大腦之勢,人的主體性被削弱……這一切說明,中國知識分子也遭遇到道德、精神、價值方面的危機,當下的中國也面臨着一定程度的人文精神危機。因此,我們有必要關注這一新興學科的發展,利用中國豐富的人文傳統資源,建立自身的人文史研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方法上,我們可以采取拿來主義的态度,但也要注意其價值屬性。所謂以普遍的、普世的諸如此類面目出現的說法,背後都隐藏某種價值訴求與理念寄托,諸如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等價值觀,究其本質都是想把自身的标準變為普世的标準,其實現的基本路徑是通過技術霸權到知識霸權,最終形成自己的話語體系、知識體系、學術體系與學科體系,并加以推廣。這是我們在借鑒、研究這門新興的人文史學科時必須留心的。
《光明日報》( 2016年10月0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