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訊的故事·憶述】
兒時,我每出家門,至鄰莊玩耍,或至三裡路外的高作鎮上購筆墨,母親都要叮咛再三,防備被狗咬,小心失足落水。1954年,我在鹽城中學讀至高二,因病辍學,次年夏,申請退學,以社會青年身份,考入複旦大學曆史系,從本科到研究生,讀了八年多,畢業後,在上海師範大學任教,後調入中國社科院曆史所。複旦大學是教我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暢遊的偉大母親,而其校訓“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是指路明燈,照亮我前進的道路,更似母親的叮咛,要終身記取,切實遵行。1964年5月,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顧炎武北上抗清說考辨》,經答辯委員會投票通過。走出複旦大學大門,已逾半個世紀,而母校複旦校訓,一直像母親的叮咛,時時在我耳邊回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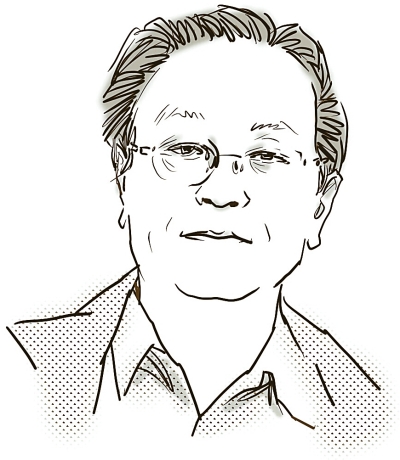
王春瑜素描 郭紅松繪
校訓源自《論語·子張》:“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事實上,這正是複旦大學優良校風的體現。以我就讀的曆史系而論,教我們世界古代史的教授周谷城,在課堂上多次告誡我們,要于學無所不窺,由博而約。他本人就是個典範,他不但精通外語,更精通史學,以一人之力,寫成《中國通史》《世界通史》,20世紀40年代由開明書店出版。1927年,周谷城投身湖南農民運動,任湖南農會秘書長,打土豪,反封建。大革命失敗後,他到上海教書,是著名的反蔣愛國的民主教授。
又如教授周予同,在課堂教導我們,不管見到什麼書,都要翻翻,要懂得目錄學、版本學,又教導我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回憶他與周谷城在五四運動中參與火燒趙家樓,親眼見到匡互生點火的情景。20世紀40年代,他們是反蔣、反獨裁、争民主的“上海大學教授聯合會”主席,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我研究生時的指導老師陳守實,是梁啟超的弟子。抗戰時,他投筆從戎,參加新四軍,任蘇南行署文教科長。戰争環境下,常要夜行,他眼睛近視很深,騎馬甚不便。粟裕同志勸他還是返滬到大學執教為好,他才重回教育崗位。
三位老師以及教授蔡尚思、譚其骧、王造時、程博洪等都是“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的楷模,我荷蒙教誨,幸何如也。
我在複旦大學讀本科時,遍讀文史書籍,換過三個借書證,讀研究生時,在善本書室,有多種康熙初年的刻本,如《砥齋集》《海右陳人集》等,還是我第一個撣去書上的灰塵,以前無人讀過。研究生畢業論文通過,等待分配時,又蒙蔡尚思師特别關照,給我一把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室(内部)的鑰匙,使我看了包括漢奸、托派、無政府主義者等等的書,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知識。我關心國事,心憂天下。我是1967年冬上海第一次炮打張春橋的“1·28”事件的策劃者之一,并寫了“點将錄”傳單。為此,受到張春橋的走狗徐景賢、徐海濤、楊一民、張惠民之流的迫害,我先後三次被隔離審查,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被平反才停止。在喪失自由的日子裡,我“切問而近思”,徹底反思“文化大革命”。從1977年至1979年,我先後發表了《究竟誰是牛金星》《株連九族考》《“萬歲”考》《燒書考》等雜文。《“萬歲”考》發表後,更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
20世紀80年代初,我清醒地看到,貪官日多,民甚厭之。為了總結中國曆史反貪的經驗教訓,我主編了近百萬字的《中國反貪史》。此書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由中國出版集團、人民出版社重版,并獲得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事實證明,古今往事千帆去,唯有校訓一篷知。我将牢記母校複旦校訓,繼續前行,生命不止,奮鬥不止。
(王春瑜先生原為我院曆史學系教授)